不被接納的青春:當年輕人躺平於街頭 在社會邊緣尋找希望

●本文摘選自寶瓶文化出版之《街頭的流離者──一名街頭社工與無家者的交會微光》。👉 前往琅琅書店購買電子書,立即閱讀!

文/楊小豌
「被社會淘汰」的年輕人
被認為「年紀輕輕卻不工作」的人,在主流社會中被淘汰後,來到街頭仍必須躲在角落中,離群索居地生活。他們的經歷,常常讓我想起我們這個世代青年的憂愁和壓力。
第一次見到阿奇的時候,我故作鎮定的外表下,心裡其實感到驚訝。除了他手中提著的基金會招牌袋子,根本沒有任何一個徵象能看出他正在流浪的狀態──因為太年輕了。二十餘歲的阿奇,臉上戴著一副斯文的眼鏡,還背著學生用的書包,只是裡面裝的不是書,而是生活用的物品。
和阿奇對話時,鮮少有眼神交會的時刻,因為他習慣低著頭,嘴角微微下垂,說話聲音低到必須非常專注才能聽清。
待在街頭的這幾年,因為一點也不像典型街友的外表,每每去排隊領取物資時都很容易引來閒言閒語:「這麼年輕,不去工作,來這裡跟老人家一起領什麼物資?」有時一些衝突就這麼擦搶走火地上演。因此他不得不多找幾個發放資源的單位,倘若這個地方對他不友善,就設為拒絕往來戶,再也不踏足。
其實為了要取得那些「免費」物資,付出的代價也是不輕鬆。我好幾次看著阿奇背著沉甸甸的行囊,拉鏈層的縫線都快撐到極限,他匆匆忙忙掐著時間要前往下一個慈善單位,要是錯過規定的時間,就得空手而歸。
放棄求職之前
阿奇並不是大學一畢業就沒工作的。只是在工廠工作的那段日子,面對同事之間充滿張力的人際相處,心裡的壓力和焦慮逐漸累積到臨界值。每天進入工廠,周遭有心或無心的言語,都讓他心跳加快、手指顫抖,恐慌的感受漫布全身……
一直到多年後的現在,盜汗的狀況仍然經常在半夜纏上他。
批判的聲音如影隨形,壓垮了原已脆弱的精神狀態──最後阿奇崩潰離職,此後便陷入長時間的停滯難行。留在家中和父親之間的衝突也越來越多。離家的姊姊試圖將他接過去一起生活,本是期待弟弟度過這段過渡期後,能自己工作、存錢租屋,卻也逐漸對於他始終跨不出家門的窘境感到無力。
於是阿奇離開姊姊家、遠離家人,來到街頭,找到一處公園的涼亭展開新階段的流浪生活。
作為一名在民間協會服務的社工,我相對不必承受民眾或個案陳情抗議帶來的壓力,能夠以較輕鬆的心態與個案交流。互動過程我注意到,阿奇時常對公部門社工表達不滿。但從這些言談中,我發現與其說討厭別人,其實他真正討厭的是現在的自己。
「都是因為我長得太年輕、不夠高也不夠壯,才會去哪都被看不起,工作也不順利。你們都不懂啦!」
他批評政府與社工的無能,認為整個社會都在集體逼迫他走向絕路。認為職場不歡迎他、慈善單位對他存疑,而那些認為他「擺爛又無所事事」的人根本不瞭解他。
我一方面想讓他覺得這些表達有被聽見,一方面又希望能在眼前的僵局中找到可施力的破口,試著說:「我沒參與過你那些受到其他人排斥的過往,也不曉得那些讓你害怕的情境是怎麼發生的,但我相信你一定有機會找到一個適合你的工作崗位。我並不覺得你的身高或外表有什麼問題。如果你願意,我陪你再嘗試一次,說不定會遇到不一樣的結果啊。」
阿奇不以為然,依然覺得沒有人可以理解他,用漠然的神情拒絕和我一起重新嘗試,眼神低垂,仍是緊抓著自己的信念:「我就是被社會淘汰了。我就是得了某種無法治療的疾病。」
社工的無力
儘管不相信醫師有辦法幫助他改善任何問題,他終於聽從社會局社工的建議到身心科看診。一進入診間,便直截了當地向醫師表達:「我很不舒服,病得很嚴重。可以幫我開身心障礙證明嗎?」
醫師答道:「我沒辦法現在就開證明,至少要穩定看診六個月後才能做評估。」
聽到這番話,他的身體彷彿豎起一層防備,往後靠在椅背上,用平淡卻帶刺的語氣回應:「醫生,你根本不相信我說的吧?你是不是根本就覺得我在裝病?」
說完他便奪門而出,醫師如何回應已經不再重要,顯然,這段醫病關係在他心裡是毫無信任基礎的。
雖然他曾多次看診,但從未接受過醫師開立的藥物,也不認為自己的病症是可以治療改善的精神疾病。他的目標僅是獲得身心障礙手冊,以便後續申請生活補助,這是在不算短的流浪歲月中,他從一些長輩身上觀察到的生存策略。
「反正那些批評我沒有用的閒言閒語和幻覺,永遠也不會消失,醫生根本幫不了我。」
服務到這樣的個案樣態,對社工來說是很不容易的:他以強勢的張揚姿態求助,希望助人工作者可以「照著他期待的方式」協助;同時獨自承受著孤獨而動盪,在青壯年階段過著消極、絕望的生活。
不只一次,社會局社工認真地連結服務資源,最終卻換來阿奇的陳情,指責社工態度不好。社工本來是想讓他和專業的身心科醫師聊聊,尋求可能的改善方案,到頭來卻被阿奇指控為強迫就醫。
我和阿奇的互動並不多,幾次看著他來到據點,在等待衣服烘乾的過程百無聊賴地滑手機、玩遊戲,我試著靠近與他聊天,卻總感覺像面對一道堅硬的銅牆鐵壁,捉摸不透他的內心世界。他固執地認定,那些無法直接幫助他獲得補助的服務都毫無意義。
其實和街上許多朋友建立信任關係的過程,本就需要長時間的互動累積,但是對於像阿奇這樣經常展現「全世界都欠我」態度的人,我的態度也逐漸變得能少招惹最好,避免熱臉貼冷屁股。
即便我願意同理街友的困境,面對這類服務對象時,也會因為想避開非必要的麻煩,而在初期的會談及瞭解後,漸漸選擇被動地消極應對。
事實上,正如同大學時社工概論課本會教的,「個案才是自己問題的專家」。社工能否提供有效能的服務,關鍵往往取決於身在苦難中的當事人是否有動機想尋求改變。若缺乏這一份個案主體的內在意願,無論社工擁有再多本領與熱情,也可能最終只是一場徒勞,甚至沾得一身汙泥。
如果回家這麼簡單就好了
有次聽阿奇說:「反正再多過幾年以後,即便我老了、殘了,也還是可以和其他長輩一樣到處排隊領便當、領物資和紅包,不會餓死。」
看著這個年輕人在流浪的歲月中,越來越被街頭的生態同化,鬥志全消,我心裡感到惋惜和擔憂。但當他來到我們的據點休息時,我只是寒暄問候,並不給予評價、質疑或責備。
我選擇不在他會在意的傷口上撒鹽,尊重他選擇的生存方式。即便我無法完全理解他的過去,仍然相信有某些原因讓他走到今天這個狀態。
然而,其他同樣在據點休息的大哥、大姐,未必能夠什麼話也不說。
臨近過年,不管是平時只能睡在朋友家地上的黃伯,還是同樣在街頭露宿的阿張哥,明明某種程度來說,大家都是失了家才會在這裡相聚的漂泊者,卻對年輕的阿奇多了幾分倚老賣老的說教姿態,甚至像唱雙簧般給阿奇灌各種心靈雞湯。
「快過年了,要回家,知道嗎?」阿張哥某天沒頭沒腦地冒出一句。
「對呀,要回家。」黃伯也跟著應和。
阿奇正在攪拌手中的飲料,聽到這話突然停下動作,抬起頭反問:「如果回家這麼簡單,我現在就不會在這裡了啦!你要不要自己先回家給我看?」
阿張哥被頂得愣住,沉默不語。
眼見場面尷尬地僵住,我忍不住打圓場:「每個人的狀況都不一樣,我們不用去講其他人的事情。」
阿奇沒再說話,只是戴了耳機上樓獨處。自此,他更加避免和其他無家者聚在一處。
他曾試圖聯繫家人,但幾次嘗試後發現,那道家門早已對他關上。而如今自己依舊一無所成,回家後,又如何能被接納呢?
我們怎能確認自己永遠不會被淘汰?
阿奇總說:「我就是被社會淘汰了啦。」這句話,讓我不禁反覆咀嚼。
事實上,這句話並不陌生。在街頭,無數大哥大姐也曾這樣說起自己。「這個社會」指的是誰?它憑什麼淘汰人?
如果這個社會只能接納符合某些條件的人,一旦掉落於這些篩選條件之外,就成為被淘汰掉的失敗者,那我一點也不想參與這種現實又殘酷的社會。我又怎麼能確定自己永遠都在「圈內」,永遠不會成為下一個被淘汰的人?
身心疾病會讓人被淘汰;抗壓性不夠高的人會被淘汰;甚至渴望追求社會認可,也可能讓人被淘汰……
我在街頭見過一些人,正因為曾經汲汲營營地追逐功成名就,向那些曾看不起自己的人爭一口氣,或是投入大量心力和錢財,只為了在一場場考試失利中再拚一次機會……最後的下場卻是人瘋了,家散了,房子沒了。
想要的沒得到,原先擁有的健康和家人也在追逐的過程中失去了。
比如阿船大哥,他說:「我以前是家族裡受敬重的長子,現在這樣落魄能看嗎?」阿船大哥曾經風光一時,多年前的一場車禍奪走了一切。腦中風及血管性失智等疾病讓他的健康急速惡化,如今的他,有時瘋癲、有時恍神,徘徊於街頭。
越深入思索這個社會的運作,越感到毛骨悚然:面對這些因主流的社會價值觀而自我厭棄的人們,他們的痛苦不僅來自物質條件的貧困,我對他們心中那座牢籠亦感到憐憫與悲哀。
我們常提醒一起參與關懷的志工:「每個人會流浪、失業的歷程和原因都不一樣,不要太快給建議或是評論,要多聽少說。我們的生活經驗差異很大,不能把自己預設的標準套用在對方身上。」
然而,這似乎就是人們難以擺脫的天性。即便是身處相似境遇的人,也很容易把別人的難題想得太簡單。
特別是像阿奇這類被認為「年紀輕輕卻不工作」的人,在主流社會中被淘汰後,他們來到街頭,仍不得不忍受四處可遇的冷言冷語,因而選擇躲在角落,離群索居地生活。他們的遭遇,常常讓我想起我們這個世代青年的憂愁和壓力。
曾聽過一位年輕的無家者分享自身的苦惱,讓年齡相近的我心有戚戚焉。
「也許別人看我年輕,才三十幾歲而已,怎麼不去找個穩定的工作。其實我十五歲就出社會了,這十幾年,我覺得自己只是困在迴圈裡,拚命賺錢、大把花錢。有一天我就突然覺得這種生活不知道意義在哪,我有個心裡的坎過不去,試著過躺平的生活,看看會怎麼樣,反正這輩子也存不到錢買房子。」
不落下任何人
從這些實驗著「躺平生活」的人們身上,總會啟發我去思考《少即是多──棄成長如何拯救世界》這本書當中,關於「成長」的討論。當我們擁抱的世界觀是「適者生存」,並認為只有符合某些條件的人值得「被幫助」,那麼那些無法適應城市生活的人,又該去哪裡安身立命?有房子的只能長年隱居於黑室,沒房子的必須在外面找到不被驅逐之處落腳。
但「他們」的故事,其實也是「我們」的故事。他們的低谷,或許是我們曾經走過的過去,亦或是未來將面臨的境地。小至個人的生病、事故、失業,或是關係的背棄、生意失敗,大至疫情、天災、戰亂,每一層風險都可能使人失去立足之地,我們身處的環境比我們想像的更脆弱。
不只這些因為「被社會淘汰」而感到失落挫敗的年輕人,需要擁抱新的眼光來看待自己與他人。我想,身處在這樣一個時代,我們都需要新的眼光來看待世界,重新定義成功與價值。
我們每個人活在什麼樣的迴圈裡?又是用著怎麼樣的標準來判斷自己和他人?
當我們擁抱著「適者生存、不適者淘汰」的思維,又有誰能保證自己永遠適合生存?
有沒有可能,我們一起,盡可能不落下任何人?
●本文摘選自寶瓶文化出版之《街頭的流離者──一名街頭社工與無家者的交會微光》。👉 前往琅琅書店購買電子書,立即閱讀!
加入 琅琅悅讀 Google News 按下追蹤,精選好文不漏接!逛書店
延伸閱讀
猜你喜歡
贊助廣告
商品推薦
udn討論區
- 張貼文章或下標籤,不得有違法或侵害他人權益之言論,違者應自負法律責任。
- 對於明知不實或過度情緒謾罵之言論,經網友檢舉或本網站發現,聯合新聞網有權逕予刪除文章、停權或解除會員資格。不同意上述規範者,請勿張貼文章。
- 對於無意義、與本文無關、明知不實、謾罵之標籤,聯合新聞網有權逕予刪除標籤、停權或解除會員資格。不同意上述規範者,請勿下標籤。
- 凡「暱稱」涉及謾罵、髒話穢言、侵害他人權利,聯合新聞網有權逕予刪除發言文章、停權或解除會員資格。不同意上述規範者,請勿張貼文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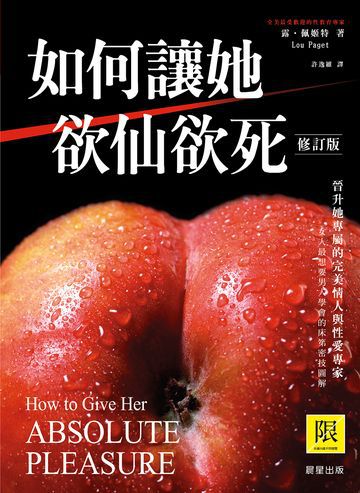







FB留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