吳明益導讀海明威《太陽依舊升起》:他站著寫出一個世代的太陽

文/吳明益(國立東華大學華文文學系教授)
專文導讀:站著寫出一個世代的太陽 關於海明威的《太陽依舊升起》
※本文含部分小說情節,請斟酌閱讀
1
初讀海明威(Ernest Miller Hemingway, 1899-1961)並不是當時中學生必讀的《老人與海》,而是在我書架上仍然存在的,書華版宋碧雲翻譯的《戰地春夢》(A Farewell to Arms, 1929)與《戰地鐘聲》(For Whom the Bell Tolls, 1940)。何明憲先生在老師賴慈芸的指導下,曾對這兩本書的流傳譯本做了非常詳細的調查,宋碧雲的版本除了部分誤譯以外(但比其他版本少),也常出現過度跟隨原文,因此產生了句子與句子間讀起來缺乏關聯性,以至於讓讀者不能理解的狀況。比方說下面這段:
我躺在平底車廂的地板上,與帆布下的槍械為伍,全身又冷又濕,飢腸轆轆。 最後我翻個身,改為俯臥,腦袋趴在手臂上。膝蓋僵麻,但是它的功能始終叫人滿意。(宋碧雲,1978:259)
「它的功能始終叫人滿意」顯然不是中文裡會描述膝蓋的句子,何明憲認為這樣的譯法流失了海明威質樸簡練文字的特色,因為英語使用者一讀就知道是形容膝蓋,中文譯本的讀者卻要轉個彎才能明白。不過當時我當然不懂這些,反而被這種難以名狀的敘述吸引,並且以為這就是「海明威風格」。
而後我當然讀了海明威的所有中文譯書,其中一本最讓我迷惘的就是《太陽依舊升起》(The Sun Also Rises, 1926)。我能在圖書館找到的幾個版本中,有的譯為《日出》或《旭日初升》,還有一個版本甚至譯為《妾似朝陽又照君》(這就像《羅莉塔》翻譯為《一樹梨花壓海棠》一樣)。這些譯本讀起來就好像不同的作者,寫出的不同書。不過即使英語能力不好的我也能看出來,這幾個名都沒有譯出原書名「also」的慨歎,而裡頭關於鬥牛的段落讀起來都沒有讓人心頭一緊的感覺。這本海明威最早的長篇小說,就此被我漸漸遺忘。
2
一九二六年七月二十一日,據海明威自述他就是在生日的這一天開始在瓦倫西亞(Valencia)動筆寫《太陽依舊升起》。這時的海明威因為短篇小說集《我們的時代》(In Our Time, 1925)的出版而有了一定的名氣,但被認為受到舍伍德.安德森(Sherwood Anderson, 1876-1941)的影響。傲氣仍在的海明威隨即寫了《春潮》(The Torrents of Spring, 1925),這本書戲仿了安德森的作品《黑色的笑聲》(Dark Laughter, 1925),一開始沒有人願意出版這本快手寫出的有爭議的作品,稿子到了傳奇編輯麥可斯威爾.柏金斯(Maxwell Evarts Perkins)手裡才得以出版。書出版後,海明威並沒有獲得好評,安德森也漸漸和海明威疏遠。
《太陽依舊升起》動筆時,正如小說裡所安排的情節,他和新婚的太太哈德莉正要去搶七月二十四日開展的節慶鬥牛表演的好座位。我認為海明威此刻的心是浮動的,因為「每個和我同輩的作家都已經寫出了第一本小說,我卻連一個段落都生不出來」。興許是節慶的氣息激發了他的感受,他利用早上在床上寫,整個節慶期間都沒停,然後出發去馬德里繼續寫。
「那裡沒有節慶,所以我們弄到一個有桌子的房間,用大錢換來舒服的寫作環境。飯店不遠處,街角就是阿瓦雷茲巷(Pasaje Alvarez),有一間挺涼爽的啤酒屋,我也去那裡寫。最後實在是熱到寫不下去了,我們就去了昂代。在那片又長又寬又美的沙灘旁,有一家便宜的小旅館,入住後我寫得非常順利。接著我們北返巴黎,回到我們那間位於鋸木廠樓上的公寓,地址是原野聖母院街一一三號,在家裡完成了初稿,距離動筆當天已經六週。」(《海明威.最後的訪談》2022: 44-45)
也就是說,這本小說是在四十二天內寫就的,而其中的幾個主人公,也不斷地來往於巴黎、西班牙或紐約,最後聚集在西班牙聖費爾明節(San Fermin)慶典上。
海明威把初稿拿給小說家內森.艾許(Nathan Asch)看,艾許用帶有濃濃波蘭口音的英語回答:「你說你寫了一本小說?這是小說嗎?這根本是遊記。」於是海明威到奧地利的施倫斯(Schruns)改稿,最終仍把小說裡的「旅行」刪除了部分,留下了西班牙溪流的釣鱒魚之旅和到潘普洛納(Pamplona)看鬥牛這兩件事。
出版後《太陽依舊升起》成為當年度最暢銷的小說,小說扉頁上寫著這本書送給妻子哈德莉和兒子約翰(他的小名正是書裡主角的暱稱Jack),然後他就離婚了。不但離婚,這本書也進一步造成他與家族更深的決裂。海明威出生於芝加哥市郊一個叫做橡樹園的小鎮,這個小鎮是清教徒聚集的地方,因此,小時候的海明威除了母親的藝術才能、父親狩獵釣魚的嗜好外,還有清教徒式的教育。
但叛逆的海明威終究無法接受,他離鄉背井擔任記者、投入戰場,走上寫作之路。早在他第一本短篇小說《三個故事和十首詩》(Three Stories and Ten Poems)傳回家鄉時就飽受批評,因為海明威的小說常常把自己親朋故友的名字寫進小說裡。《太陽依舊升起》出版後,母親寫了信說:「這是當年度最汙穢的小說之一。」父親也說:「海明威又寫了一本齷齪的小說。」海明威則像一個拳擊手說自己不會被擊倒。
「汙穢」與「齷齪」指的應該是小說裡一眾角色在性上面的觀念,以及他們不怕冒犯上帝的言論。他的朋友作家哈洛.羅伯(Harold Loeb)則因為小說裡的猶太裔美國人羅伯特.寇恩(Robert Cohn)感到憤怒。兩人原本友情深厚,甚至一起參加了潘普洛納鬥牛節──這本小說開始寫的地方。哈洛的女友後來真的也就跟海明威的另一個朋友混在一起,兩人為此幾乎拳腳相向。哈洛認為羅伯特寫的就是他,把他寫得更懦弱卑下。這本書出版後,兩人當然就決裂了。
海明威似乎全不在意得罪同行。在巴黎熱烈招待海明威的美國作家葛楚.史坦(Gertrude Stein, 1874-1946)曾對海明威說了一個汽車修理廠工人的故事,提到雇主指著他說:「你們全屬失落的一代(lost generation)。」她認為這句話可以代表海明威這個世代。
海明威並不以為然,他說:「她的說法完全是危言聳聽。我認為我們這一代人也許在許多方面受了傷害,但是除了那些死者、殘者和已經證實的瘋子外,如果說我們都迷失了方向或者受到了損害,那我無論如何都不相信。」「我們是失落的一代?不對。我們是堅強的一代。」
不過,等到出版《太陽依舊升起》時,他卻把這句話放到了扉頁上,寫了「你們全屬於失落的一代」。
歷經戰爭的這個世代當然一定失落了什麼,但lost也可以說是迷失、迷惘、不清楚,畢竟這個世界在短短的時間後,大戰又隨之而來。這世間有什麼是可以掌握、如星辰或太陽依舊升起那樣明朗、明確的呢?
3
根據統計,海明威作品中和戰爭有關的高達二十六部(長短篇),而和鬥牛或釣魚、打獵相關的必然也相當,甚至更多吧?戰爭是人類的群體鬥爭,鬥牛、釣魚或狩獵則常常是孤獨或小組與自然生命的戰鬥。它遠比戰爭更容易掌控一些,但危險並無二致。與這兩者相比,更不能掌控的,同時也危險的,或許就是海明威筆下的愛情吧?
《太陽依舊升起》一開始出場的是富家子弟兼小說家羅伯特,他被傳說是普林斯頓大學的中量級拳王,曾離過婚,現在和掌控欲強的情人法蘭西絲在一起。而敘事者「我」雅各.巴恩斯(朋友們暱稱他杰克)是因打仗脊椎受傷失去性能力的記者,在他身邊的則是充滿魅力的布蕾特。
故事圍繞著這幾個人物,引出一批戰後被激流衝擊,四處尋找生命方向的年輕人,他們聚在咖啡廳高談闊論、飲酒、調情、跳舞,或者隨興到遠方釣魚、看鬥牛、旅行。有人靠貴族贊助生活才能進行自己的藝術創作,也有人揮霍無度到要和人伸手借一頓飯錢。
其中我認為真正驅動故事的人物,是因為無法在巴恩斯身上獲得滿足,坦白自己「見人就勾搭」的艾敘理夫人布蕾特。她和羅伯特單獨去度假,又跟追求者麥可.坎貝爾保持親密,隨後又愛上鬥牛士羅美洛……。
海明威並沒有花太多筆墨描寫巴恩斯的心理狀態,只在第四章布蕾特搭著禮車離開時寫到:「在白天,凡事全以硬心腸對應,這是再簡單不過的措施,但夜深了又是另外一回事。」
和《戰地春夢》和《戰地鐘聲》不同,《太陽依舊升起》並沒有實際描寫戰爭場面,更多的是描寫釣魚和鬥牛。事實上,光是描寫到釣場的路程風景就花了好幾千字。我在想,如果光把小說裡海明威描寫風景、釣魚、鬥牛的字句抽出來,應該足以和人與人之間的互動、對話旗鼓相當。甚至不該說是旗鼓相當,小說最後那場羅美洛被羅伯特揍以後上場的鬥牛描寫得如此精采,如果拿掉或譯得不好,整本小說幾乎就會喪失精神:
他在牛的前方站對位置,從鬥牛布抽取寶劍,順著刀鋒瞄準牛。牛看著他。羅美洛對牛喊話,一腳踏一踏。牛衝過來,羅美洛等候牠,紅布低垂,舉劍對準牠,穩住立足點。接著,他無需向前邁一步,紅布向下一揮,牛頭跟著來,轉瞬間紅布消失了,羅美洛向左抽身閃避,人牛就此合一,刀鋒高高刺進兩肩中間,結束了。牛想再往前走,腿卻不聽使喚,身體左搖右晃,游疑不決,隨即腿軟下跪,羅美洛的兄長從他身後俯身上前,手持小刀,想刺進牛頸近牛角的部位。
第一次,他失手。他再戳,這次牛倒地了,抽搐著,不再動作。羅美洛的兄長一手握牛角,另一手持刀,仰望總統包廂,滿場是舞動中的手帕。」
羅美洛把象徵鬥牛士榮譽的,割下來的牛耳送給布蕾特,他們倆相視一笑。最後巴恩斯卻目睹布蕾特「把牛耳裹進我的手帕,連同幾根穆拉蒂菸屁股,全塞進潘普洛納的蒙托亞飯店房間床頭櫃抽屜的最深處。」
4
成名後的海明威愈來愈少接受訪談,特別是在他獲得諾貝爾文學獎後。他身上兩百多處迫擊砲彈舊傷,加上飛機失事的腦震盪、內臟破裂,森林大火中的灼傷,讓他暫時失明、失聰,感受或許已非鬥牛士,而是傷痕累累的牛。
但他在我的印象裡,始終是那個在《巴黎評論》訪談中,說自己總是站著寫作,只有極少數時用打字機,狀況好的時候一天能用掉七支削好的二號鉛筆,但那些文字多數被他修改作品時刪掉了的作者。
當然還有他在文學圈子裡的壞人緣,他跟福克納,費茲傑羅都不太好,葛楚.史坦、舍伍德.安德森、 T. S.艾略特、福特.馬多克斯.福特(Ford Madox Ford)或多或少都被他消遣過,其中有曾經的好友、啟發的前輩。不過我們現在是用超級望遠鏡來看這些逝去的作者了,這些或許都不再重要,何況如海明威自己說的:「偉大的詩人不一定有資格當女童軍或童子軍幹部,抑或是青年的典範。」(《海明威.最後的訪談》2022: 63)
我曾經以為閱讀這些經典作家的作品,是引領我度過寫作難關的重要途徑,但漸漸我發現,理解他們在什麼樣的情況下,寫出那樣的作品更是迷人。畢竟曾經讀者鍾愛的表現可能已成標本,曾經動人的風采終究也是上一個世代的明媚陽光。

作者:海明威 (Ernest Miller Hemingway)
出版社:麥田
出版時間:2024年2月27日
在《太陽依舊升起》裡,這些夾雜在戰火和現代性萌生的年輕人,一開始壓根不為什麼高尚的文學或藝術目標創作,在未婚妻眼中,羅伯特寫作就是為了紅回紐約而已。他們唯一擔心的是沒有人讀他們的作品,或者同輩比自身更受關注。他們徘徊在菁英咖啡館(Le Select)、穹頂咖啡館(Dome)、達摩瓦咖啡館(Damoy)、丁香園咖啡館(Closerie des Lilas)和拉維尼舞廳,千里迢迢到另一個國家只為了看一場慶典、一次鬥牛或者釣鱒魚……。
換到我們這一代、下一代也是一樣。社群媒體的活動,那些新興的各種文學藝術集會與個性化的咖啡館,那些網路的辯論與或明或暗的勾心鬥角,都是為了展示人類創造出的華麗的繁殖羽。
但當然也不僅僅如此。那樣猛烈的青春裡除了激情還有其他。海明威在接受喬治.普林普頓(George Plimpton)訪問時說:「小說家要是沒有正義感,無法感覺不公不義的存在,那就乾脆別寫小說了,還不如去幫特殊學校編畢業紀念冊。」盲目的激情、嫉妒、野心,或者再加上「我們不知道的其他理由」與「某種方向的正義感」,才是一代又一代創作者投身期間的推進器吧。
所以在出版將近百年後,我能重讀手上這本宋瑛堂先生的新譯本,特別感覺以現在來重看《太陽依舊升起》的意義是:它寫的可能不是「失落的一代」,而是追求「活著」感覺的「每一代」。
這是因為我們以「新的一生」去讀海明威當時面對的「唯一的一生」。《大西洋月刊》總編輯勞勃.曼寧(Robert Manning)說,某次他們在紐約安靜吃晚餐時,海明威突然抬起頭來語帶驚訝地說:「你知道嗎?我認識的所有美女都變得愈來愈老了。」自己也老了的海明威發現,太陽依舊升起,但一代逝去,另一代會前來。只是新的一代已經不是他曾經認識的了。
聽聞麥田將陸續出版《太陽依舊升起》、《戰地春夢》和《戰地鐘聲》,我不禁想起自己迷戀後兩本書的高中時代。那時在沒有人的房間裡,我偶爾從書頁的世界裡抬起頭的雙眼,也許如夢初醒,看著窗外剛升起來的太陽。那些在鬥牛場上驚呼、戰場上受苦、在咖啡廳裡追求情人與藝術的一代,終歸寫出了一本一本的書、畫出一幅一幅的畫、做了一個一個的夢,活過一個又一個的青春,然後在其間老去,新的一代繼續造夢,繼續老去。夢境當然不會永遠是甜美的,夢境最可貴的地方在於迷惘、不可理解,以及不會完全重複。
而海明威站著寫出了一個世代的太陽,那旭日初升的陽光只屬於他們,迷惘、迷失或失落也屬於他們的。不,或許透過這樣歷久彌新的小說,我們會發現,那也同時屬於我們的。
●本文摘自麥田出版之《太陽依舊升起》(諾貝爾文學獎得主海明威的人生三部曲I)。
加入 琅琅悅讀 Google News 按下追蹤,精選好文不漏接!逛書店
延伸閱讀
猜你喜歡
贊助廣告
商品推薦
udn討論區
- 張貼文章或下標籤,不得有違法或侵害他人權益之言論,違者應自負法律責任。
- 對於明知不實或過度情緒謾罵之言論,經網友檢舉或本網站發現,聯合新聞網有權逕予刪除文章、停權或解除會員資格。不同意上述規範者,請勿張貼文章。
- 對於無意義、與本文無關、明知不實、謾罵之標籤,聯合新聞網有權逕予刪除標籤、停權或解除會員資格。不同意上述規範者,請勿下標籤。
- 凡「暱稱」涉及謾罵、髒話穢言、侵害他人權利,聯合新聞網有權逕予刪除發言文章、停權或解除會員資格。不同意上述規範者,請勿張貼文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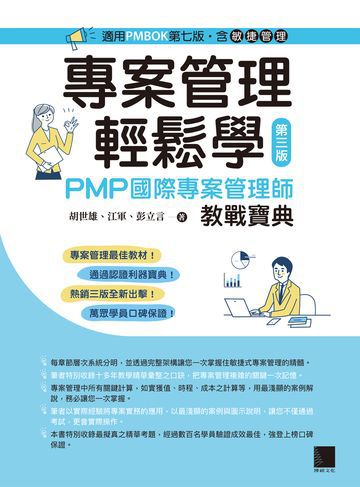





FB留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