沒有個人主義英雄的戰爭──海明威《戰地鐘聲》導讀

美國文學史上最重要的創作,海明威最真實也最具深度的作品─《戰地鐘聲》,從對自由的保衛到理想的幻滅,深切描繪戰爭中人性與生死的糾結。這部二十世紀最廣為人知的反戰文學經典,也與《太陽依舊升起》、《戰地春夢》、《老人與海》並列海明威最傑出創作。(編按)
●本導讀摘自麥田出版之《戰地鐘聲(諾貝爾文學獎得主海明威的人生三部曲III)》。👉 立即前往琅琅書店購買電子書,馬上開始閱讀!
文/蔡秀枝(國立臺灣大學外國語文學系暨研究所教授)
沒有個人主義英雄的戰爭(導讀)

作者:海明威(Ernest Miller Hemingway)
出版社:麥田出版
出版時間:2024年10月31日
一九四〇年海明威(Ernest Miller Hemingway, 1899-1961)出版《戰地鐘聲》,為剛剛結束的西班牙內戰(1936-1939)立下一座沒有鐫刻英雄名字的文學紀念碑。《戰地鐘聲》一書甫出版就得到許多讚揚,被《紐約時報》譽為海明威的最佳小說和美國文學史上最重要的小說之一。
《戰地鐘聲》的英文書名《For Whom the Bell Tolls》是取自英國詩人、聖保羅大教堂首席主教約翰.鄧恩(John Donne)在一六二三年於病榻沉思生死時所寫下的散文作品《緊急場合的靈修》(Devotions Upon Emergent Occasions,共二十三節短文)裡的〈沉思十七〉(Meditation XVII):
No man is an island, entire of itself; every man is a piece of the continent, a part of the main. If a clod be washed away by the sea, Europe is the less, as well as if a promontory were, as well as if a manor of thy friend’s or of thine own were: any man’s death diminishes me, because I am involved in mankind, and therefore never send to know for whom the bell tolls; it tolls for thee.
沒有人是一座孤島,能自外而周全;
每個人都是大陸的一片,是整體的一部分;
如果海水沖掉一塊土,歐洲就縮減,如同山岬少了一塊,
如同你朋友或自己的莊園少了一塊;
任何人的死亡都是我的損失,因為我是人類的一員;
所以永遠別問喪鐘為誰而鳴;
它為你而鳴。
約翰.鄧恩在此篇章裡深刻地體悟到「人非孤島」。「每個人都是大陸的一片,是整體的一部分……任何人的死亡都是我的損失,因為我是人類的一員;所以永遠別問喪鐘為誰而鳴;它為你而鳴。」也正是人與人之間保有的那種無法截斷的互相聯結與關涉,才因之得以串聯起人類的共同命運。於是某一個人的死亡總或多或少地牽扯出其他人的削減、甚至死亡。
所以戰地喪鐘並不僅只是為小說主角羅伯.喬登這位參加西班牙內戰的美國人而敲響,它也為書中喪生的西班牙游擊隊員、法西斯黨人、共和軍、國民軍、以及所有因為戰爭與衝突而犧牲的人民哀悼。然而此喪鐘的鳴響不僅代表了以上種種死亡的告知,也象徵性地藉由其音聲的比喻,由此而彼,慢慢地浸透、聯結了所有聽見鐘聲的人。
海明威曾在一九三七年二月寫給他第二任妻子寶琳(Pauline Pfeiffer)的信裡指出,西班牙內戰就像是一場歐洲戰爭的預演。海明威《戰地鐘聲》的書名引用約翰.鄧恩「喪鐘為你鳴」的譬喻,也可能是有意將它延伸作為預示人類共同命運的警鐘,用以象徵性地警示那未知的、潛藏的、可能將引發第二次世界大戰機鋒的種種悄然醞釀,繼之隱隱不絕地傳遞著為未來戰爭喪生者的哀悼。
海明威文字敘事的簡潔與小說人物對話的直白,讓人性層出不窮的自私、懦弱、背叛與算計等,均無從隱匿。羅伯因為炸橋計畫必須尋求游擊隊協助。僅僅發生在四天(其實真正依時數而計還不滿三天三夜)裡的事件,卻能經由小說人物間的溝通交際,點點滴滴地勾串延伸,將單一炸橋事件,輻輳出一個可以被約略預想勾畫的西班牙內戰遠景。
藉由詩人約翰.鄧恩的人際聯結(interconnectedness)概念和喪鐘音聲傳播的蔓延與擴散的寓意,海明威將這場有著嚴謹的地域劃分和時間限定的西班牙內戰,翻轉演繹成飽含文學寓意的,關於人類貪婪、自私、失德與殘暴掠奪下的共業,因之譜出一場展現並預示人類共同命運的失序浩劫。
缺乏個人主義英雄的戰爭:人非孤島
故事的主角羅伯.喬登是炸橋事件的謀畫者。整部小說從他開始探勘地形,尋求帕布羅帶領的游擊隊協助,安排準備炸橋的計畫(用以斷絕並阻擋法西斯國民軍的增援,並以此拉開共和軍展開攻擊的序幕),到國民軍可能知悉共和軍的攻擊計畫而派遣偵察機、轟炸機前來,羅伯因此派人與戈茲將軍聯繫必須要停止炸橋計畫(後因軍隊裡的種種拖沓,以致消息太晚送達而未果),再到當地開始下起五月雪(另一游擊隊首領聾子和其隊員們的藏匿蹤跡因此暴露)、游擊隊首領帕布羅偷竊炸藥、引信與雷管夜逃,炸橋計畫最終不盡完美,並以羅伯和許多游擊隊員的喪生告終。
故事始於羅伯的地形探勘,以羅伯用其將死之軀做生命的最後一擊(射殺帶隊追擊炸橋者的國民軍騎兵中尉,以爭取讓愛人瑪麗亞、皮勒和帕布羅安全撤離)為終結,首尾聯結一氣呵成。從嚴格的情節、意義與作用上來檢視,炸橋這個事件最終對整個戰爭攻擊計畫而言並不是最重要與不可或缺,因為這個炸橋行動可以被以各種理由喊停。戈茲將軍在下達炸橋命令給羅伯時都直接承認:誰能保證他的命令不會更改?誰能保證攻擊不會取消,不會延後?誰能保證攻擊能在預定時刻六個鐘頭內開始?有哪一次攻擊能完全遵照計畫?真實的戰爭永遠都充滿各種未知的變數,這就是現實的人生與生命的真正樣態。
羅伯身為一個爆破者,可以是一個獨自策畫工作、懷著浪漫情懷的外國志願軍,但是他並不是霸氣的戰爭英雄。他的計畫必須要依賴全然陌生的游擊隊成員的通力合作才能成事。在帕布羅表態拒絕參加炸橋計畫之後,羅伯並沒有如其他人所暗示與盼望地開槍殺死帕布羅。反而是帕布羅的妻子皮勒強烈贊成並支持他的計畫,因此凝聚了其他游擊隊員。羅伯需要皮勒這位果敢決斷又堅韌信賴共和軍的女性,以及她燉煮的、能撫慰所有人的溫暖食物。
同時他更渴望與驚喜年輕美麗的瑪麗亞的愛情,讓他感受到強烈的愛欲,並理解到經由深刻的愛的力量,他或許能夠將與瑪麗亞在一起的這三天不到的七十個小時,當成兩人有如已經親密生活在一起七十年,宛如他們已經度過了相親相愛的一生,而且他可以為她犧牲自己的生命。同時他也必須突破自己不擅長且不喜社交、傾向單獨行動的習慣,才能順利完成炸橋任務。
這些正是他最終得以從炸橋事件中學習到的愛、社群經驗與人生現實。海明威將整個事件與所有小說人物凝聚成一幅人非孤島,人人依靠人人的眾生圖像。這是一個不凸顯,甚至沒有個人主義英雄的戰爭。海明威藉由《戰地鐘聲》描繪出他對戰爭的看法,並為人類的戰爭與任意無差別的屠殺立下一個用以警醒世人的,沒有鐫刻凸顯個人英雄的文學紀念碑。
殺戮現場:毀滅與生機
在海明威的敘事視角下,不論是共和軍或國民軍,在戰爭裡都分別扮演著殘酷殺戮者的角色。沒有哪個群體是無辜的。而其中人物的造化則各憑緣法。皮勒對羅伯講述了她所在小鎮的一場殘暴屠殺,那也是帕布羅如何崛起的重要事件。帕布羅領著眾人趁夜包圍軍營射殺傷兵、國民兵、衛兵,接著率眾占據小鎮開始掃蕩所有法西斯分子。
雖然剛開始時這些農民並不想參加殺戮,但是在種種刺激下,他們開始暴躁地拿起連枷等農具殘忍地殺害一個又一個法西斯分子。但是皮勒在目擊這些法西斯分子被一一處決後,卻從中感到抱歉。因為被殺者未必個個都是什麼十惡不赦之人。
瑪麗亞也向羅伯說起她的村莊被國民軍屠殺的情形。在村長父親與母親的死亡後,她落入國民軍手裡,被粗暴的剃光滿頭長髮、被殘暴地集體性侵與監禁。作為一個倖存者,她必須忍辱背負身體和心靈的雙重傷害。但是羅伯的愛情讓瑪麗亞變得勇敢,願意敞開心胸向羅伯傾訴一切加諸其身的暴虐。羅伯對她的珍視與愛,讓瑪麗亞得以經由敘述個人的悲劇來直面自己的不幸。在愛人面前不隱瞞她恥辱的遭遇,用誠真與愛來對待自己與羅伯的情感。
在戰爭的陰影與死亡的壓力下,這份真誠的愛與勇氣代表著歷經殘暴戰火肆虐與人性卑劣侮辱後錘鍊出的純粹,即使短短不足三天,也足以濃烈燃燒並照亮兩人短暫交叉的生命,最終支持瑪麗亞堅持為她自己(同時也為了終將從她的生命中退場的羅伯)繼續活下去。
這是海明威對無情戰火與殘暴人性肆虐下,依舊堅持的脆弱生命與堅貞濃烈的愛情的謳歌——真愛不論相聚的時長,它是從生命的狹小莖脈裡孕育綻放的、救贖的花朵。它教會了瑪麗亞堅強,也教會羅伯為愛犧牲自己。
然而,並非所有參與戰爭的人都嗜殺成性、毫無人性。大雪過後國民軍騎兵中尉發現了聾子與其帶領的游擊隊員的行蹤,率隊擊斃他們並下令割下這些游擊隊員的首級。在領著隊伍繼續前行時,中尉心裡並不覺得驕傲。
他只感到行動之後的空虛。割人首級太野蠻了。但是他們必須留下殺死敵人的證據以獲頒軍功。騎兵中尉面對割人首級一事,不得不以戰爭之名來合理化他的殘殺與處理敵方屍首的手段,以自身的理智來壓制情感的分裂,因為這些殺戮行為都是在戰爭的名義下,集體地對對方陣營的所有人進行的無差別掠殺,而且雙方在戰鬥場上其實也互相在贏與輸之間扮演著虐殺者與被虐殺者的角色。
戰爭裡沒有道德,戰場上的殺戮也不允許個人懷抱悲情或是與政治理念相違背的原則。以戰爭之名,屠殺因此成為一個平等的代名詞。而給受傷的夥伴補上一槍、協助其死亡,則變成良善的手段,因為可以讓無法脫逃的夥伴免於遭受對手殘忍的虐待與迫害。
從羅伯私下的自問自答裡也可以看到被軍令壓制下道德觀的質問,讓他用以支撐在服從軍事命令背後的反法西斯信念已面臨傾頹:
你已經殺過多少人了?他自問。不知道。你認為自己有權殺死任何人嗎?沒有,但我得下手。你殺的人有多少是真正的法西斯分子?很少。但他們都屬於跟我軍對立的敵方。……難道不知道殺人是錯的嗎?你知道。但你還是殺人?對。而你還百分之百相信你是基於正確的理由?對。
最後羅伯只能對自己說:「你最好別再想了。這對你和你的任務都很不好。」羅伯以職業上的遵守軍令與執行命令,來逐退情感與道德上的虧欠。老嚮導安索莫因為有著信仰,堅持不殺人。但是當他的任務是盯哨即將要進行炸破計畫的橋時,他還是開槍殺了一個哨兵。他知道這與他的信仰背道而馳,可是戰爭的狀態迫使他必須如此。
他只能退而求其次,堅持一旦戰爭結束,就是這個非正常狀態的結束,那麼屆時人們都要懺悔他們曾經做過的殺戮。面對人生中的這些變數、突發狀況和非正常狀態(因為炸橋事件而被牽連在一起的命運),海明威筆下的人物各自展現了面對問題的可能姿態與解方。
死亡凝視下的生命之歌海明威對戰爭中殊死雙方的立場與政治信仰並不支持。於他,生命的意義或是與死神的搏鬥,必須有著生命的尊嚴和榮譽。這是西班牙和西班牙人的精神。
《戰地鐘聲》裡有一段不同的生死爭戰場景。那是有關於皮勒以前的情人鬥牛士菲尼托的故事。當帕布羅和他的游擊隊員恥笑菲尼托是個懦夫、肺癆鬼時,皮勒強硬地反擊這樣的侮辱。皮勒告訴帕布羅:「你現在會怕死了。你現在覺得死掉是件大事。」她承認菲尼托隨時隨地都害怕公牛,甚至當「菲尼托俱樂部」設宴邀請他到以他的名字命名的俱樂部時,他坐在筵席間連看都不敢看那個掛在牆上被他殺死那頭牛的牛頭。但是當他站在鬥牛場中面對公牛時,他卻勇猛如獅。他所受的訓練讓他在面對公牛的爆發力與死亡的近身威脅時,堅守住他鬥牛士的自尊、驕傲與榮譽。他必須在與公牛的鬥爭中,尋找公牛的弱點進行高貴的攻擊。
但是因為他身高不太高的關係,使得他的胸部在使用技巧甩弄紅布挑釁公牛時,總難以避免地會頻繁地被公牛角橫掃撞擊,因此落下肺癆傷病。然而鬥牛士因為職業而導致的身體病痛,並不是懦弱的徽章。海明威筆下的鬥牛士即使有著身體缺陷,對於職業鬥牛場裡的生死攸關,是絕對不會棄甲怯懦遁走的。
相對於鬥牛士面對死亡的挺直腰桿、堅決面對,皮勒的先生、游擊隊首領帕布羅,卻在經歷過小鎮上的大殺四方後,懦弱地逃離了他的戰場。安索莫就直言帕布羅自從有了馬匹,就成了資產階級,開始如懦夫般害怕失去他所掌控的財產與生命。但是帕布羅無疑是有著看透現實情勢的精明,所以當他看出炸橋計畫恐怕不能成功後,就連夜偷盜羅伯的炸藥和雷管等引爆物,將之丟下山谷棄置,以此破壞羅伯的計畫。
後來他因為害怕被大家唾棄變成孤單一人,只得再去招攬另一批人馬來替補死去的聾子游擊隊。但是在羅伯炸橋之後,帕布羅就直接殺害了這個來協助他的小隊,因為他要謀奪他們的馬匹。現在的帕布羅只是一個貪生怕死的懦夫、背叛者和殺人犯,但是他有他活下去的方法。相反地,當羅伯完成炸橋任務卻意外摔斷腿時,為了讓愛人得以順利逃生,他選擇放棄與瑪麗亞、皮勒和帕布羅一起撤離,而是苦撐著受傷的身體留下來布置他生命裡的最後一擊:射殺國民軍騎兵首領,阻止他順利帶領騎兵團迅速追殺正在撤離的瑪麗亞等人。
在死亡的陰影迫近時,鬥牛士菲尼托、游擊隊首領帕布羅、和美國來的志願軍羅伯身上各自背負著生命裡難以承受的輕與重。不懼艱苦遠赴西班牙當志願兵的羅伯,猶如鬥牛場中驕傲榮耀的菲尼托,犧牲奉獻出自己的性命。
另一組游擊隊五十二歲的首領聾子,在臨死時並沒有驚慌失措,「如果人難免一死,他心想,而且顯然就是會死,我也可以死。但我真是恨透了」。此刻的聾子接受了這個討厭的事實,傷口疼得厲害,可是仍努力感受著生命勃發出的各種動能:
死不算什麼,他對死沒有想像,心中也沒有恐懼。可是活著是山坡上有風吹拂的麥田。活著是天上的老鷹。活著是在穀物的殼遭到敲打飛散,以及在這片霧濛濛中那只裝著水的陶罐。
無獨有偶地,瀕死的羅伯躺在滿是松針的地上,也感受到了壓在松針上的心臟因為即將到來的射殺行動而猛烈地跳動,一如小說的開篇裡,他躺臥在布滿松針的赤褐林地上,感受這夏日的山坡、豔陽與吹過松樹頂的微風。
當生命即將耗盡時,聾子和羅伯是幸福的,因為他們都得以重新感受與掌握生命流動的微小而純粹的力量。臨死的聾子眼下所見的是生命的力量與波動的匯聚,是不同的脈絡流動下的渾沌與艱辛,是乍現微光下的飛翔與流轉。而羅伯在生命的最終時刻,亦是感受著生命的跳動,和即將為愛人爭取到生的機會的雀躍。生命的形式與人的感知流動,即使在在不同,卻因為念想與波動而互相聯結。
從二十世紀四〇年代《戰地鐘聲》裡的戰爭圖像,轉回到二十一世紀的俄烏戰爭、以巴衝突、以伊衝突,現代戰爭機器的大幅進化,通訊機、智能手機轉瞬變裝炸彈裝置,無人機與各式經由電腦人工智慧操控的殺傷力與毀滅性倍增的攻擊武器日新月異,不只宣告戰爭機器的進化論,也見證個人主義式戰爭英雄的式微。
在人工智能時代,人與人之間的互動互聯也需要重新定義。約翰.鄧恩和海明威的叩問或許能再次提供一絲清明的洞察:人非孤島,每一個當下的波動與變換,其力都將向外影響、擴散,一如鐘聲之飄盪、綿延。
●本導讀摘自麥田出版之《戰地鐘聲(諾貝爾文學獎得主海明威的人生三部曲III)》。👉 立即前往琅琅書店購買電子書,馬上開始閱讀!
加入 琅琅悅讀 Google News 按下追蹤,精選好文不漏接!逛書店
延伸閱讀
猜你喜歡
贊助廣告
商品推薦
udn討論區
- 張貼文章或下標籤,不得有違法或侵害他人權益之言論,違者應自負法律責任。
- 對於明知不實或過度情緒謾罵之言論,經網友檢舉或本網站發現,聯合新聞網有權逕予刪除文章、停權或解除會員資格。不同意上述規範者,請勿張貼文章。
- 對於無意義、與本文無關、明知不實、謾罵之標籤,聯合新聞網有權逕予刪除標籤、停權或解除會員資格。不同意上述規範者,請勿下標籤。
- 凡「暱稱」涉及謾罵、髒話穢言、侵害他人權利,聯合新聞網有權逕予刪除發言文章、停權或解除會員資格。不同意上述規範者,請勿張貼文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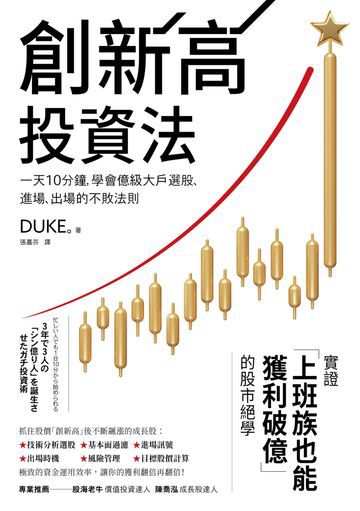







FB留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