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珮君/那殺不死我的,必使我更強大(下)——澎湖山東流亡學生血淚奮鬥史

文/沈珮君
前情提要:
好好讀書
張敏之、王培五兒孫都在美國落地生根了。么女張鑫的孫子取名時,她兒子想把外祖母「培五」的「培」字放在孩子的中間名(middle name),想了很久,取「培」諧音譯成Pearl,珍珠。不可能有更好的英譯了。
眼淚變珍珠,這似乎是一個過度美化的童話,而竟然真的發生。張敏之的子女個個學業、事業有成。張彤將自己上櫃的半導體公司「泰安」賣給神通集團後,2008年出任英特爾上海分公司總經理,2011年退休。他們多次回到爸爸老家,完成他奉獻教育的心願,在煙台二中設獎學金,並以受難者補償金捐獻一棟「張敏之教學樓」,請諾貝爾獎得主丁肇中題字,因為那也是丁媽媽的母校。
令人感慨的是,煙台鄉親有人激憤地對他們說:「張敏之、鄒鑑是我們煙台『最大的敵人』。」因為他們把煙台最優秀的青年都帶到台灣了。而這樣的張敏之、鄒鑑卻命喪台灣槍下。
「我爸是兩岸的敵人,很悲哀。」張彤苦笑。
公視記者呂培苓曾把張家的故事寫成《一甲子的未亡人》,有很細緻的訪談,根據學生的回憶,張敏之「既嚴謹又開明」,教育理念很民主,但是,對「好好讀書」這事沒得商量,「有頑固不可動搖的執著」。
「好好讀書」,也是我訪問到的山東流亡學生子女回想父母家教時,必然會提到的。這些流亡學生對於「讀書」這件事,與張校長一樣有「頑固不可動搖的執著」。這種執著來自他們各自父母的殷殷叮嚀,也是他們在流亡人生中一路不敢自棄的原因,而「一定要讀書」的自覺,也傳給了他們在台灣出生的子女。
單德興,中研院歐美研究所特聘研究員,生長在南投中寮鄉,父母是山東嶧縣人,是那群流亡學生中罕見的夫妻檔,他們在南投教書,從青春到白髮,備受當地人敬愛。單德興對童年記憶很深刻的是,家裡月底常常窮到必須跟雜貨店賒帳,但是,父母平時仍不吝給兒女買東方出版社和國語書店的注音版兒童名著,這在當時是很奢侈的支出。他們三兄妹自小都喜歡讀書,後來統統是博士。單德興兒子也是美國麻州大學學士、交大碩士。
讀書是家風。單媽媽孫萍兩、三歲就在父親教導下認字,她到老都愛看書。單爸爸單汶在澎湖被迫入伍,民國48年在國防部「木蘭計畫」下,山東流亡學生可退伍復學,單汶才以中士退役,進了員林實中,三十三歲念高三,服役十年所得只有兩套衣服、一頂蚊帳、一床被子、退伍金五百元。學校吃住都不理想,每到吃飯,坐在風沙飛揚的泥土地上,六人圍吃一盆大鍋菜,但老師熱情,同學刻苦,總算可以讀書了。
單汶、孫萍在小學任教之後,仍未忘記進修,五十多歲時一邊教書,一邊利用暑假繼續讀書,雙雙自台中師專畢業。孫萍退休前,獲得資深優良教師八德獎章,八十歲病逝。2019年單家在台灣的第四代誕生,單汶跟兒子欣慰地說:「從山東到台灣,我們兩個流亡學生,沒有白活。」單汶今年九十八歲,很可能是澎湖山東流亡學生在世最高齡者。
在國立苗栗農工任教的陳芸娟也是在父親鼓勵、支持下,從高職、二專、大學,拿到師大歷史研究所碩士,論文題目是《山東流亡學生(1945-1962)》,她是第一個拿山東流亡學生當學術論文的人,她父親陳永昌就是當年的學生。芸娟出生時,父親已四十歲,前面雖已生了一個兒子,但陳永昌特別疼愛這個寶貝女兒,芸娟也極力討他歡心:「我喜歡讀書、教書,都是因為我爸。」爸爸在苗栗山區教書,買不起兒童書,暑假時把學校的百科全書借回家給孩子讀。陳爸爸在頭屋鄉明德國小教導主任任內退休。
陳媽媽小他十九歲,他極疼愛年輕妻子,但兩人仍常常吵架,因為窮。當時老師部分酬勞是以「米」代替,但不夠吃,爸爸沒辦法借到米,媽媽從早餐店張羅到一些燒餅掰成小塊煮成糊糊一大鍋,含淚告訴他們三兄妹:「我一定會讓你們吃飽」。陳媽媽希望女兒去當美髮學徒,「洗一個頭可賺三十元」,但陳芸娟想念大學,想念歷史系,陳爸爸很高興,滿口答應:「只要你想念書,念什麼都好」,他四處借錢也要讓她讀書。
陳芸娟嫁給鄰居男孩,婆家與娘家僅一牆之隔,她早上還沒起床就可以聽到爸爸在隔壁廚房燒水的聲音。即使如此近,她出嫁時,才跟著「帶路雞」走了幾步,回頭一看,爸爸已在門旁哭成淚人。她從小就常看到爸爸哭,「我爸爸哭時很怪,他會拍大腿,先笑,然後才哭。」爸爸看平劇《四郎探母》會哭,難過、高興都會哭。他有一肚子淚。
她從小就覺得爸爸好苦,但一頭霧水,爸爸常跟她講在大陸流浪的故事,「我那時好小,連『大陸』是什麼意思都不知道」。
父親哭得讓她最心碎的一次,是他輾轉得知在大陸的老娘去世,他嚴肅地準備三牲,寫上牌位,跪在地上放聲號啕:「娘——」痛徹肺腑。他們家頂樓有設祖宗牌位,陳永昌晚年時,有一次站在頂樓跟女兒說想跳下去,陳芸娟事後回想:「他應該有憂鬱症,但我們那時不懂。」
陳永昌去世時,陳芸娟不在身邊。2017年7月13日,她應國家人權館、澎湖文化局之邀,到澎湖演講,說她爸爸的七一三故事,講著講著忽然喉頭堵住了,開始哽咽,正在此刻,她從台上看著台下的先生接了一個手機電話,用嘴型告訴她:「爸爸走了。」陳永昌用這樣的方式來跟心愛的女兒魂靈合體,讓自己的生命故事在澎湖七一三這個傷心日、這個傷心地打上句點。

一生「小心翼翼」
陳永昌一生「小心翼翼」,每一次的分別,都生怕是永別。他第一次回老家,唯恐不能再回台灣,還交代了遺言。可笑嗎?當初他離開老家,以為只是出門幾天,誰知就是永訣。他每件事情都做到無微不至,「他很怕一件事、一句話不對,就會被什麼單位『找到』。」陳芸娟去度蜜月,爸爸再三叮囑要把結婚證書帶在身上,「你們孤男寡女,小心警察會抓」。
即使他們不是在七一三事件、一二一一慘案中直接受害的當事人,但陰影一直如影隨形。現在與兒子住在龍潭「渴望村」的張天信,也是山東嶧縣人,兒子在半導體產業服務,也很會讀書,已取得美國與交大碩士,正在台大攻讀第三個碩士學位。七一三事件,張天信在現場,看到李樹民被刺傷、唐克忠被拖離現場時,血自褲管流到沙地。那些血和恐懼很難從心中抹去。
當時他只有十四歲,也去當兵,他又瘦又矮,槍比他還高,最小尺寸的軍服也無法穿,軍方只能發給他一頂軍帽,「我是全連唯一沒穿軍服的人」。張天信太小了,在軍中充滿挫折,爬樹、跳馬、吊單槓,他統統不會,「班長說我是個廢人」,當兵對他打擊很大,「我覺得人生到此沒希望了」。但他一直記得「我出來是要讀書的」,他靠收聽中廣自修英文,考上了財務學校,1970年少校退伍,1974年經過特考進了財政部,後來在支付處科長任內退休。
九十歲的他一臉頑強,很決絕地說:「我全部靠自己,我不靠任何人。」他幾乎不跟孩子談這段過去,他兒子直到七一三紀念碑立了,從新聞得知國家人權館辦的座談、展覽,從網路爬梳,才比較了解父親當年經歷過什麼事。
張天信自七一三事件後,似乎不想再與那件事、那些人有牽扯,他從不去山東同鄉會,也沒有回過老家。但是,直到現在,他深夜還會到孫子房間去,「我要看看他們還在不在」。當年就是有同學一覺醒來,旁邊的人不見了,這是多深層的害怕,七十多年揮之不去。
這些山東流亡學生,幾乎都不跟孩子提澎湖那段往事,唯恐把他們也牽連進去。但是,他們聚在一起就會談,小聲談,有時候談著談著就哭了。
政大新聞系副教授方念萱、知名主播方念華是姊妹,她們的外祖父是當年山東省府祕書長楊展雲,曾營救張敏之未成,後來積極參與平反。他是山東第一所流亡學校「湖北中學」的校長,後來繼苑覺非之後接任員林實中校長。方念萱的媽媽楊澍跟山東流亡學生朱炎、張玉法、陶英惠是員林實中同學,方念萱從小就對他們名字耳熟能詳,「我媽媽每次開同學會回來,都會說朱炎又哭了。」朱炎曾任台大文學院院長,他不是跟那群山東流亡學生一起到澎湖的,他是青島即將淪陷時,朱媽媽含淚要孩子各自逃命,他惶惶流浪到岸邊,乞求一個軍官帶他上了最後撤退的「裕東輪」到台灣。他十三歲,沒有槍桿高,後來也去念了澎防部子弟學校、員林實中。每次參加同學會,想到亂世流離的日子,想媽媽,醉後的朱炎總是哭得很傷心。
這群師生「學校家庭化,老師父兄化,學生子弟化」,親如家人,苑覺非曾身為澎防部子弟學校負責人、員林實中創校校長,替學生擔任主婚人兩百多次,家裡永遠有一大袋麵粉,隨時包餃子給學生吃,客廳也經常有學生打地鋪。他的兒子、前台大哲學系系主任苑舉正曾經覺得他爸爸是「幾千人的爸爸」,不是他一個人的爸爸。
單德興從小也看到很多「叔叔」在寒暑假進出、借宿他家,他們來時,爸媽就特別高興,他們大人常小聲講話,不讓孩子聽到。2019年國家人權館辦七一三事件七十周年特展時,單德興台北、澎湖全程聽了五場座談與演講,才更了解那段父母噤聲的歷史。
他在父母身上看到七一三事件對他們的最大影響是「謹慎」,極謹慎。在兩岸還沒有開放交流前,父母都不敢跟老家聯絡。外祖父母過世二十年後,他媽媽才輾轉得知,悲痛地請假一天,閉門追思,寫下悔罪書燒給父母,身穿縞素百日,對自己過度謹慎而沒有跟父母及時聯絡,痛心疾首。可憐父母直到去世都不知道他們是否活著。
陳芸娟謹慎的爸爸雖然也不敢跟老家聯絡,但曾請人偷偷帶了一張照片回去,一個字也不敢寫,他父母去世前至少知道兒子在台灣還活著。

心中有一個「塊壘」,
不斷湧出來
朱炎一直極度想念他那挽著柳條籃乞討的老娘,後來千方百計透過美國親人,經過香港,輾轉把他夢魂牽縈的山東老娘接到台灣,老娘快走到他的台大宿舍時,他快樂地一把背起她,一路跑一路狂呼:「娘回來了,娘回來了」。重享天倫一年,老娘就過世了。
楊展雲到台灣時,只帶了較小的孩子,長子、長女都留在大陸,後來費盡工夫,一家人總算在美國洛杉磯團聚。本來應是個歡樂時刻,但楊展雲知道兒子加入了共產黨,怒不可遏,要他跪下。方念萱回憶這一段往事時,仍感心痛:「我有一陣子對外公很不諒解,因為我大舅很可憐。在那個亂世,大舅受了很多苦,他被下放到新疆,也曾入獄,舅媽為了給他看孩子,在監獄外面把孩子舉起來給他透過鐵窗看一眼。」多麼悲傷。
楊展雲的母親在「大躍進」餓死,奄奄一息時仰問蒼天:「祢在哪?我連粥都吃不上」。方念萱感慨萬千:「這是國仇家恨。我外公和我爸爸至死都不願意回老家,不堪回首。」情到濃時方轉薄,誰的錯?誰有錯?
單德興祖母、外祖父母很可能也是餓死。他第一次陪父母回老家時,第一大事便是祭祖墳。四野蒼茫,墳在田中,沒有墓碑,沒有土塚,他跪在地上,旁邊燒著香和紙錢,隱隱覺得不遠之處的空中有魂靈,他止不住地流淚,親戚相勸,都沒辦法讓這個男兒停淚,「我覺得心中有一個『塊壘』,不斷湧出來」,直到那個堵在心頭的東西哭化了,他才終於止淚。單德興後來回想,一方面覺得不可解,一方面覺得「我在哭時,彷彿有祖先在旁與我同哭。」
皈依法鼓山的單德興溫厚篤實,性情淡定,但在台大外文系同學替朱炎老師賀七十五歲壽時,他又一次失控。同學替朱老師精心挑選了一件防風防雨的GORE-TEX冬衣做生日禮物,單德興致詞時提到「我父母也是山東流亡學生」,淚湧不停,語塞良久,而經常為此流淚的朱老師那天反而異常平靜。朱炎已經病弱,第二年冬病逝,僅七十六歲。他駕駛電動輪椅,後座搭載著朱師母,台大一景再也看不到了。
淚史,歷史能不能不再有淚?(下)
加入 琅琅悅讀 Google News 按下追蹤,精選好文不漏接!逛書店
猜你喜歡
贊助廣告
商品推薦
udn討論區
- 張貼文章或下標籤,不得有違法或侵害他人權益之言論,違者應自負法律責任。
- 對於明知不實或過度情緒謾罵之言論,經網友檢舉或本網站發現,聯合新聞網有權逕予刪除文章、停權或解除會員資格。不同意上述規範者,請勿張貼文章。
- 對於無意義、與本文無關、明知不實、謾罵之標籤,聯合新聞網有權逕予刪除標籤、停權或解除會員資格。不同意上述規範者,請勿下標籤。
- 凡「暱稱」涉及謾罵、髒話穢言、侵害他人權利,聯合新聞網有權逕予刪除發言文章、停權或解除會員資格。不同意上述規範者,請勿張貼文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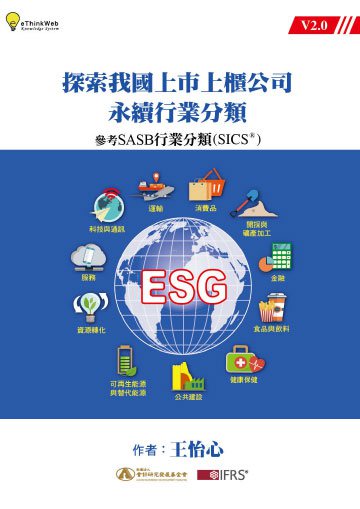







FB留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