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匕首X鋼匕首雙重大獎肯定!《看穿謊言的女孩》劇力萬鈞完美續集

曾以《死活不論》擊敗史蒂芬‧金、J.K. 羅琳等強敵,勇奪英語系犯罪小說界的最高榮譽──英國犯罪作家協會金匕首獎的邁可‧洛勃森(Michael Robotham),後又推出席捲文壇的懸疑系列作《看穿謊言的女孩》,二度拿下金匕首獎,成為極少數能兩次榮獲金匕首的「殿堂級」作家,奠定其文壇地位。《看穿謊言的女孩》系列描繪倖存於弒親滅門悲劇的犯罪心理學家,借助一名冷酷暴戾卻能揭穿所有謊言的問題少女,協力辦案的故事,系列續作《謊言誕生的房間》,獲得Goodreads讀者超過5000則五星滿分評價、英國犯罪作家協會「鋼匕首獎」最佳驚悚小說得獎作。(編按)
文/邁可‧洛勃森(Michael Robotham)
賽勒斯
二○二○年五月
時值春末,早晨冷冽,一艘小木船從迷霧中現影,隨著每次掃槳往前滑行。港口裡的水面如鏡,導致每一圈漣漪向外擴散、延展並在觸及船首後漸漸散去的樣貌都清晰可見。
我吐出的氣息讓房間的窗戶起霧了,於是把袖口拉向掌心,擦拭一小塊窗玻璃好讓自己能看得更清楚。她終於來了,我已經等了六天。我走過步道、造訪燈塔,也吃膩了歐尼爾酒吧餐館的菜色。我還讀了早報、三本特價小說和聽當地的酒鬼向我訴說他們的人生故事。他們大多是漁夫,雙手的指節像薑一般粗糙扭曲,就算沒有刺眼陽光,他們看見光線時依然會瞇起眼睛。
她倚向木船,把防水布翻開,裡面有一些塑膠箱和紙箱,每隔兩週會來採買日用品。她雙手捧著箱子,越過地上的鵝卵石從海邊步上階梯。她沿著海濱步道行走,我的視線一路跟著她,看著她行經拉上鐵門的售貨亭和觀光禮品店,走向一個內部燈火通明的小超市。她越過一綑報紙後敲門,一位鼻子和臉頰紅通通的中年男子拉起百葉窗,向她點頭示意,接著轉動單閂鎖,領她進去之前先掃視街道,也許是在尋找我,他知道我在等著。
「莎夏.赫普威爾?」我問道。
她伸手到風衣外套的口袋,有那麼一刻,我想像裡面有武器,一把捕魚刀或一罐催淚瓦斯。
「我叫賽勒斯.海文,我是個心理學家,我寫過信給妳。」
莎夏從我旁邊擠身而過,開始拿取架上的日用品,把推車裝滿雜貨,挑選一袋袋的米和麵粉、一些罐頭蔬菜和燴水果。我跟在她後頭穿越走道,同時她在拿草莓果醬、保久乳和花生醬。
「七年前,妳在北倫敦的一間屋子裡找到一個小孩,她躲在一間密室裡。」
「你認錯人了。」她魯莽地回道。
我從外套口袋裡拿出一張照片。「這是妳。」
她匆匆瞥了一眼那張照片,然後繼續屯購乾貨。
這張照片裡有一位穿黑色緊身褲和深色上衣的年輕志願警察,她抱著一個髒兮兮像野獸的小孩走進醫院大門。小女孩的臉被一頭打結的亂髮遮住,抱著莎夏的樣子宛如一隻無尾熊攀著樹木。
我又從口袋裡拿出另一張照片。
「這是她現在的樣子。」
莎夏忽然停下動作,忍不住望向那張照片。她想知道那個小女孩──天使臉女孩現在變成什麼模樣。那個藏在密室的女孩,當時是個小孩,現在已是青少女了。照片裡的她坐在水泥長椅上,穿著破牛仔褲和寬鬆的套頭毛衣,毛衣其中一手的手肘處有個洞。她把頭髮留長了,染成金色,朝著鏡頭板著一張臉,沒有笑容。
「我還有其他張照片。」我說。
莎夏別開眼,伸手拿在我身後架子上的通心麵。
「她的名字是艾薇.寇梅克,現在住在安全的兒童照護之家。」
她繼續推著推車往前走。
「告訴妳這些有可能讓我坐牢,《第39章條例》禁止任何人洩露她的身分、所在的地點或拍攝她的照片。」
我擋住她的去路,但她又往前踏一步避開我,於是我跟著她的步伐移動,就像我們在走道上跳舞一樣。
「艾薇隻字不提她在那間屋子裡發生過什麼事,那就是為什麼我來這裡,我想了解她的遭遇。」
莎夏推開我往前走。「去看警察的報告吧。」
「我需要比那更多資訊。」
她走到冷藏區,打開掀蓋冷凍櫃後開始在裡面摸找物品。
「你是怎麼找到我的?」她問。
「很不容易。」
「我爸媽有幫你嗎?」
「他們很擔心妳。」
「你讓他們身陷危險。」
「怎麼說?」
莎夏沒回應我,逕自把購物推車停放在結帳櫃檯附近,接著又推了一台。那位紅鼻子男已經不在櫃檯了,不過我聽見他在樓上走動的腳步聲。
「妳不能一直逃跑。」我說。
「誰說我在逃跑了?」
「妳在隱匿行跡,我想幫助妳。」
「你辦不到。」
「那讓我幫助艾薇吧。她很不一樣,與眾不同。」
咖啡廳就在郵局旁邊,位在同一棟低矮的石砌建築裡,可遠眺一座橋和潮溝。桌椅排放在小徑上,上方有個條紋圖案的雨篷飾以聖誕彩燈,黑板上有手寫的菜單。
一名穿圍裙的女子正在把倒過來的椅子扳正,並清理椅子上面的灰塵。
「廚房要七點才開始營業。」她說話有康瓦爾口音。「我可以先幫你們泡茶。」
「謝謝妳。」莎夏回道,選了一個面向門的軟墊長凳,那裡可以一覽小徑和停車場,老習慣。
「我自己來的。」我說。
她不發一語地注視我,坐著時膝蓋併攏,雙手放在大腿上。
「這個村落很美。」我說話時望向漁船和遊艇,看見第一道陽光灑落船桅的頂端。「妳住這裡多久了?」
「這和我們要談的事情無關。」她伸手到口袋裡,拿出一條護唇膏,塗抹在嘴唇上。
「給我看那些照片。」
我拿出其他四張照片,攤開來擺在桌上。這些照片是艾薇現在的模樣,她即將滿十八歲。
「她很常染頭髮。」我說。「會染成不同的顏色。」
「她的眼睛一點也沒變。」莎夏說,用大拇指撫過照片裡艾薇的臉,彷彿在描繪她的輪廓。
「她的雀斑在夏天時長出來了。」我說。「她很討厭雀斑。」
「我超羨慕她的長睫毛。」
莎夏把那些照片並列排在一起,改變順序好讓她方便檢視,或者這是某種無法言喻的設計感。「他們找到她的父母了嗎?」
「沒有。」
「DNA比對呢?失蹤人口?」
「他們把全世界都搜遍了。」
「她後來發生什麼事?」
「她受到法庭保護,法庭給了她一個新名字,因為沒人知道她真正的姓名。」
「我以為一定會有人來招認她。」
「那就是我來這裡的原因,我在想艾薇可能對妳說過些什麼,給過妳某些線索。」
「你這是在浪費時間。」
「可是妳是找到她的人。」
「僅此而已。」
接著我們又陷入更久的沉默,莎夏雙手插進口袋裡,定住不動。
「你知道的有多少?」她問。
「我讀過妳的陳述,足足兩頁。」
擺動門從廚房由內而外敞開,剛才那位女侍者為我們送上兩壺茶。莎夏打開茶壺蓋子,將茶包上下搖動。
「你去過那間屋子嗎?」她問。
「去過。」
「也看過警方的報告?」
我點點頭。
莎夏把茶倒入杯中。
「他們在樓上的前臥室裡找到泰瑞.波蘭德,他被綁在椅子上,嘴巴被塞住,是被折磨至死的。強酸滴入他的耳裡,眼皮被燒光。」她打了個哆嗦。「那是北倫敦多年來最大宗的謀殺案件。我當時是在巴內特警局擔任志願警察,當時刑案室位在二樓。
「發現時波蘭德已經死兩個月了,也因此警方花了很久的時間辨認他的身分。他們發布一張他臉部的模擬畫像,他的前妻打熱線進來,提及波蘭德的名字時,大家都很驚訝,因為他是個無名小卒,只有過一些像是攻擊和竊盜等輕微的犯罪紀錄。大家原本以為這個案件會和黑幫扯上關係。」
「妳當時有參與調查嗎?」
「當然沒有。志願警察只是雜工,做些狗屁倒灶的工作和負責社區聯繫而已。我那時在樓梯間經過調查這起殺人案的警員旁邊,也在酒吧裡偷聽到他們交談。當他們找不到任何線索時,就開始猜測波蘭德是個惹錯對象的毒販。當地人大可放寬心,因為這是壞人在自相殘殺。」
「妳怎麼看待這件事?」
「我沒資格評斷。」
「妳當時為什麼被派去那間屋子?」
「我不是被派到那間屋子,而是去那條路上調查。那裡的街坊鄰居在抱怨東西不見了,車庫和花棚裡有些零散的東西被偷竊,於是我的長官派我去詢問他們狀況,就當作是公共關係的實作練習。他稱之為「麵包和馬戲」 ,讓群眾開心。
「我在那條街走上走下,敲門詢問關於竊盜的事,可是所有人都只想談論那場謀殺案。他們總會問相同的問題:『你們抓到兇手了嗎?我們需不需要擔心?』每個人都自有一套推論,但沒有人真的熟識泰瑞.波蘭德。他二月份住進那間屋子,但並未進一步和鄰居來往。他會揮手打招呼、遛狗,但多半保持神祕。
「大家對那些狗在意的程度更甚於波蘭德。他死在樓上的好幾個星期,他的兩隻德國牧羊犬在後院的狗屋裡挨餓。不過其實牠們並沒有餓到,有人一直在餵牠們食物。人們說那些殺手一定回來過,意思是他們比起人類更在乎那些狗。」
女服務生再度步出廚房,這次她的手裡拿著一個黑板,把黑板撐在一張椅子上。
「那些竊盜案件呢?」我問。
「被偷竊的物品中,最值錢的是一件羊毛衣,一位女士用來鋪貓的床。」
「還有呢?」
「蘋果、餅乾、剪刀、早餐麥片、蠟燭、麥芽糖、火柴、雜誌、狗飼料、襪子、撲克牌、混和乾草糖等等,噢對了,還有一個艾菲爾鐵塔的水晶球。我記得那個,是因為那是住在對街一個小男孩的東西。」
「喬治。」
「你和他談過了。」
我點點頭。
莎夏似乎對我透徹的調查感到訝異。
「喬治是唯一看過天使臉女孩的人。他原本以為在樓上窗戶旁看到的是個小男孩。喬治揮揮手,但那小孩並未揮手回應。」
莎夏點了藍莓麥片粥、柳橙汁並加點了茶,我選了全英式早餐和雙份濃縮咖啡。
她已經放鬆心情、脫下外套了,我注意到她的衣著頗為貼身。她把落到臉龐的幾縷髮絲撥到耳後,我努力回想她讓我想起的人,是一位女演員,不是剛出道那種新星,而是凱瑟琳.赫本。我媽喜歡看老電影。
莎夏繼續說下去。「鄰居都無法解釋小偷是怎麼進家門的,可是我懷疑他們可能讓窗子開著,或者門沒上鎖。我打給長官,給了他一張清單。他說是小孩子搞的鬼,要我回家。」
「可是妳沒有就此罷手。」
莎夏搖搖頭,頭髮像在燃燒。「我正要走回車上時,注意到有兩位油漆工人正把東西打包到小貨車上。七十九號正在重新翻修,要準備出售。於是我和那位年輕工人和他的老闆小聊了一下。他們抵達時房子的狀況很糟,牆面上有洞、屋裡有破水管和撕破的地毯。氣味是最糟的一部分。
「年輕工人名叫托比,他說這間房子鬧鬼,因為有東西一直不見,像是無線電和吃了一半的三明治。他的老闆笑稱是托比自己很常忘東忘西的,所以可能是他自己忘了三明治的去向。
「托比的老闆給了我鑰匙之後,他們就開著小貨車走了。我上樓巡視每個房間,還記得當時心裡納悶為什麼泰瑞.波蘭德要租這麼大的屋子。四間臥室在北倫敦並不便宜。他預先付了六個月的房租,而且是付現,在租賃合約上用的是假名。
「我在階梯上坐了幾個小時,然後用防塵罩鋪成一張臨時權充的床,讓自己保暖。到了午夜,我真恨不得自己已經回家了,也好希望可以有個枕頭或睡袋。我覺得自己很蠢,如果警局有人發現我為了監視某個空屋子而在裡面待一整晚,我會成為辦公室的笑柄。」
「後來發生什麼事?」
莎夏聳聳肩。「我睡著了,夢到泰瑞.波蘭德的脖子和額頭都被皮帶綁著,強酸滴入他的耳裡。你覺得在侵蝕開始之前,他會先感覺到冰冷的液體嗎?他能聽見自己的尖叫聲嗎?」
莎夏的身子在顫抖,我注意到她的手臂起了雞皮疙瘩。
「我記得我醒來後用拳頭敲敲頭,想努力把強酸敲出耳朵。就在那時,我感覺到有人正在看我。」
「在屋子裡嗎?」
「對。我大叫出聲,可是沒人回應。我把燈打開,把屋子從上到下全部仔細找過一遍,可是屋子裡全無異狀,除了廚房水槽上方的一面窗之外,那面窗開著。」
「而妳之前把它上鎖了。」
「我不能百分之百確定。」
女服務生打斷我們,為我們送上餐點,莎夏每吃一匙都會朝粥吹氣,她看著我排列眼前切成三角形的吐司,這麼一來那些茄汁焗豆就不會沾到蛋,蘑菇也不會碰到培根。這是一場軍事行動,在盤子上管理我的食物。
「那間房子裡後來發生什麼事?」我問。
「到了早上我開車回家,沖個澡後躺上床,一覺睡到下午一兩點。我爸媽想知道我在哪裡過夜,我告訴他們我參與一場監視行動,讓這件事聽起來像是重要的警察工作。我騙了他們。
「那天是星期六,我原本那晚要和朋友出去,可是我沒有。我開車去超市,買些爽身粉、手電筒的備用電池、柳橙汁和一個家庭包的巧克力棒。接近午夜時分,我回到荷斯安路,悄悄地打開門。我那時穿的是我上健身房的裝扮,黑色緊身褲、拉鍊外套和運動鞋。
「我從樓上開始把爽身粉撒在地上,沿著樓梯撒下來,經過走廊再到廚房。每個房間我都不放過,在空蕩蕩的地板上撒了薄薄的一層粉,當電燈關著的時候肉眼是看不見那些粉末的。後來我把屋子重新鎖上,回到我的車裡,爬進睡袋,把座椅往後調後就睡著了。
「一位牛奶送貨員在黎明時分把我吵醒,我聽見瓶子在木箱裡碰撞的框啷聲響。我進到屋裡,用手電筒照著地板。地上有腳印分頭走向兩個方向,樓梯上下與沿著走廊到廚房。腳印停在水槽前面,就在我前一晚發現打開的窗子底下。我沿著腳印走,跟著走上樓,穿過樓梯平臺後走進主臥室。腳印就在衣帽間的衣架子下方消失了,這就好像有人忽然消失無蹤,或被史考提 隱形傳送了一樣。
「我仔細研究這個衣櫥,把衣架子撥到一邊,手指沿著踢腳板摸了一遍。我輕敲石膏板時發現裡面的聲音很空洞,所以把袖珍折刀的刀片塞進鑲板邊緣,前後拉動,每拉一次鑲板就移動一些。我用身體的重量推動鑲板,可是有東西似乎在反推回來。最後我直接用手指勾住愈來愈寬的縫隙,用力往後拉。石膏板被我推向一邊,在衣櫥後方竟然有個爬行空間,大約八呎長、五呎寬,在遠處那端有個斜天花板,空間朝遠端愈來愈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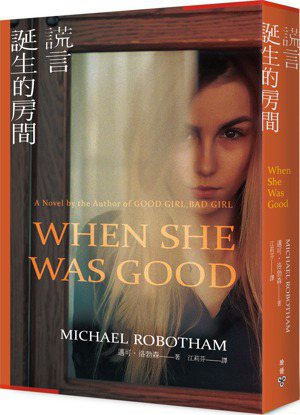
作者:邁可‧洛勃森(Michael Robotham)
出版社:臉譜出版/城邦文化
出版時間:2022年10月27日
「我用手電筒照地上,看到一些食物的包裝紙、空水瓶、雜誌、書本、撲克牌和艾菲爾鐵塔水晶球。『我不會傷害你的。』我說。『我是警察。』
「沒有人回應,所以我用嘴巴咬著手電筒,以跪姿爬進那個洞裡。這空間裡像是空無一人,只有一個木箱子塞在天花板和地面之間。我移近腳步,說:『別害怕,我不會傷害你的。』
「我來到箱子旁邊,用手電筒往箱子裡面照,看到那裡有一綑破布,而且開始蠕動。原先緩慢的動作後來變得急促,接著忽然間,有個東西從我身旁衝出去,我伸手要抓那塊破布,但它還是從我的指尖溜走了。在我來得及反應之前,那生物就不見蹤影了。我必須再往回穿過鑲板回到臥室裡。就在那時,我聽見門把轉動的聲音,和小小的手敲擊樓下窗戶的聲音。我從樓梯欄杆瞥過去,看見一道黑影沿著走廊快速奔向起居室。於是我跟在後頭,看見有一雙腿從煙囪裡伸出來,就像是煙囪清掃工人在試著往上爬一樣。
「嘿!」我說。那人影迅速轉身,朝我低吼。我一開始以為是個小男孩,但後來發現不是男生,而是個小女生。她用一把刀直指著自己的胸腔,就在心臟的位置。
「她的模樣……我永生難忘。她的皮膚好蒼白,導致在她臉頰上的灰塵看起來像瘀青。她的睫毛和眉毛都很濃密黝黑,好像洋娃娃一樣。她穿著一件褪色的牛仔褲,膝蓋處有個破洞,上衣是一件胸前有北極熊圖案的套頭毛衣。我以為她七歲,也許八歲,或者可能年紀更小。
「我被她的狀態和那把刀震懾住了。是什麼樣的小孩會威脅要拿刀刺死自己?」
我沒回話。莎夏雙眼緊閉,彷彿在腦海中重現當時的畫面。
「『我不會傷害妳的。』我說。『我叫莎夏,妳叫什麼名字?』她沒回我。當我手伸進口袋,她又把那把刀往自己的胸前刺得更用力。
「我們在那裡一定坐了超過一小時,全都是我在說話,我告訴她關於爽身粉和廚房窗閂的事,她完全沒反應。我拿出我的搜索令,把它舉高,我說這能證明我是志願警察,那幾乎等同於受訓中的警察。我說我能保護她。」
莎夏原本看著空碗,而後她抬起頭。「你知道她做了什麼嗎?」
我搖搖頭。
「她看著我的眼神,讓我覺得自己好糟糕。那眼神裡充滿了絕望,不抱一絲希望。這就好像把一顆石頭丟進黑色的井裡,等著它掉落到底部,但它從來沒掉到井底,而是一直不斷地在墜落。那讓我很害怕。還有她的聲音,刺耳而沙啞。她說:『沒有人能保護我。』」
加入 琅琅悅讀 Google News 按下追蹤,精選好文不漏接!
逛書店
延伸閱讀
猜你喜歡
贊助廣告
商品推薦
udn討論區
- 張貼文章或下標籤,不得有違法或侵害他人權益之言論,違者應自負法律責任。
- 對於明知不實或過度情緒謾罵之言論,經網友檢舉或本網站發現,聯合新聞網有權逕予刪除文章、停權或解除會員資格。不同意上述規範者,請勿張貼文章。
- 對於無意義、與本文無關、明知不實、謾罵之標籤,聯合新聞網有權逕予刪除標籤、停權或解除會員資格。不同意上述規範者,請勿下標籤。
- 凡「暱稱」涉及謾罵、髒話穢言、侵害他人權利,聯合新聞網有權逕予刪除發言文章、停權或解除會員資格。不同意上述規範者,請勿張貼文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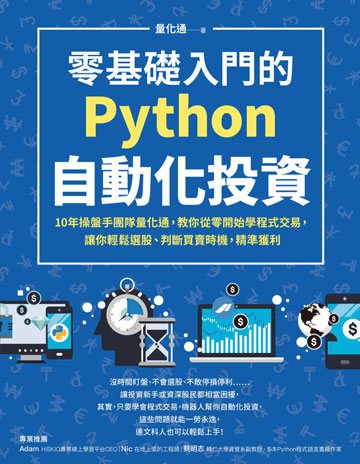




FB留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