龍應台/動物流亡
二◯二◯年十二月二十四日早晨,一輛三噸半的小卡車停在家門口。
這是我在台灣南方屏東縣潮州鎮的旅寓,三年前離開台北來照顧年邁的母親的地方。小鎮生活三年,已經使我發現我是一個可以離開都市濃稠而迷人的社交生活、不以鄉間清簡生活為苦的人。
卡車裝滿了不重要的東西:書和生活用品。重要的東西在我自己開的吉普車上:兩隻貓,兩隻小土狗,七隻母雞,分別是芝麻、枇杷、巧克力、布朗妮,加上三隻來亨雞,羽毛雪白、身材高䠷,像三胞胎,分不清誰是誰,因此都叫「白雪」。
載著一個「動物園」上路,從屏東潮州到台東都蘭要經過三段路:沿著台灣海峽往南五十公里,橫穿中央山脈由西往東三十公里,出山後,沿著太平洋岸往北七十公里。
安置動物時,費了一點心思。貓籠放在前面駕駛座旁,因為貓咪對移動會極度不安,需要隨時伸手安撫。狗籠和雞籠在後車廂並置。流浪狗媽媽所生的兩個娃娃,達爾文和鴻堡,才剛斷奶,四腿短短,身體肥肥,走路歪歪斜斜,就是兩個會跌倒的肉球團團。他們四腳朝天也能呼呼大睡,睜開眼睛不知今夕何夕,所以山遠路遙車子晃動都不是問題。雞籠下面鋪了一個塑膠盤,接住糞便,裡面則鋪上一層厚厚的稻草,讓母雞們趴在那裡。羽毛蓬鬆的她們,像極了穿著大圓裙跳華爾滋舞的婦人,剛剛跳完舞,正在托腮慵懶地喝著下午茶。
滿載動物上路,慢慢開,不煞車,不超車。台灣海峽灰藍色的水,閃過一株又一株木麻黃,風景像河水一樣流過去,如同我的生命。
鄉村歌曲輕快的節拍裡有貓咪撒嬌的喵喵聲和母雞自言自語的咕咕聲。等候綠燈時回頭看,狗狗睜開萌萌的、黑鈕釦般的眼睛,看一眼旁邊的雞,又睡了起來。
✽
離開台灣海峽轉入大山,天空開始飄雨,灰色的雲迅速聚攏,在山峰與山峰間形成絹布上積水太多的潑墨,往下渲染。名叫「丟丟」的貓突然發出悲戚的叫聲,一聲接一聲。叫「丟丟」是因為,她是一隻被人丟棄在野外的幼貓,像隻老鼠那麼小,我聞聲而覓,從草叢裡撿起來,抱了回家。
伸出右手,把手指伸進貓籠的小洞,撫摸她的耳朵,她用頭來蹭,安撫了好一會兒,漸漸安定下來,這時,母雞突然咯咯咯咯叫了起來,聽聲音,是芝麻在叫──難道她下蛋了嗎?車行駛中,無法回頭看。
沿著懸崖峭壁行駛,峭壁下是很深的峽谷,腦海突然浮起一個遙遠的、遙遠的聯想。
一九三七年八月,在日軍的砲火轟炸中,南京中央大學開始打包遷校,目的地是重慶。校長羅家倫,那時不到四十歲,有計畫地遷走四千名師生、兩千箱圖書和儀器。打包上船的,包括航空工程系拆解了的三架飛機、醫學院準備上解剖課還泡在福馬林液體裡頭的二十四具人體。農學院許多的珍稀動物,每種選出一對,諾亞方舟模式,「雞犬圖書共一船」大西遷。
但是最後,大學的附屬農場上還有上千頭不那麼「珍稀」的動物,譬如國外引進的牛和豬、雞和鴨──他們都上不了飛機,更沒有輪船可用。怎麼辦?
羅家倫校長告訴大學畜牧場的技師王酉亭說,戰亂啊,可遷則遷,不可遷,沒有人會怪你。
整個大學人去樓空之後,日軍攻破南京首都之前四天,這位技師,把個子小的雞鴨鵝兔分別裝籠,然後把籠子一個一個掛上可以用四條腿走路的牛羊豬馬,像帶著駱駝隊一樣,開始了戰爭中動物的「敦克爾克大撤退」。
從南京到重慶,用筆畫一條直線是一千五百公里,真用腳去走,可能要好幾倍。這上千個帶蹼帶爪兩隻腳的和毛茸茸、吃奶的四條腿的,不僅只是路程問題,他們得過大河,爬高山,穿森林,涉沼澤,而且,在戰爭的交火和轟炸之中穿梭,這用公里怎麼算呢?出發時,牛在頭,豬殿後。雞鴨護於其中,前後綿延四百公尺,上千隻不同的動物,由四個兩隻腳的人類帶領,怎麼走?怎麼上船、怎麼過隧道、怎麼穿過鐵軌?
他們怎麼吃、怎麼拉?怎麼睡?
而且,能想像牛和馬用同樣的速度走路嗎?豬,看到前面一攤爛泥巴而歡喜狂奔時,拉得住嗎?
在漫天烽火中千里運黃金、萬里扛國寶,是因為黃金國寶人人都說價值連城。但是戰爭爆發時,牛羊豬馬雞鴨兔算什麼呢?家禽家畜,跟中央銀行的黃金、故宮博物院的瓷器,能相提並論嗎?
✽
流亡動物大隊長途跋涉,歷經嚴寒與酷暑、砲火與檢查哨,十二個月之後,四條腿的和兩條腿的,真的走到了重慶。
這一天,冰天雪地的重慶大街上,擠滿了轟炸中倉皇逃難的人潮。羅家倫在大馬路上遇見這「蘇武牧羊」的隊伍。
……這些牲畜用木船過江,由浦口、浦鎮,過安徽,經河南邊境,轉入湖北,到宜昌再用水運。這一段游牧的生活,經過了大約一年的時間。這些美國牛、荷蘭牛、澳洲牛、英國豬、美國豬和用籠子騎在牠們背上的美雞、北京鴨,可憐也受日寇的壓迫,和沙漠中的駱駝一樣,踏上了牠們幾千里長征的路線,每天只能走十幾里,而且走一兩天要歇三五天。居然於第二年的十一月中到了重慶。我於一天傍晚的時候,由校進城,在路上遇見牠們到了,彷彿如亂後骨肉重逢一樣,真是有悲喜交集的情緒。(註一)
這一位萬里跋涉、趕著牲畜流亡一年的技師,鬚髮盡灰塵,月薪不過八十元。
羅家倫就在那兵荒馬亂、人命如蟻的路上,流著眼淚擁抱那幾個滿面塵埃的人,又低頭親吻了那睜著天真的眼睛的牛羊豬馬們。
✽
戰爭爆發時,動物園裡的動物──會怎樣?
一九四三年英美盟軍猛烈轟炸柏林,第一天的轟炸十五分鐘內,動物園裡百分之三十的動物被炸死。第二天,整個水族館被炸爆。
一九四五年蘇聯紅軍攻破柏林時,動物園本身成為巷戰區。管理員先處死了危險的動物,譬如毒蛇、老虎,避免在轟炸的混亂中毒蛇猛獸滿街跑。巷戰結束時,戰前三千七百多隻動物只剩下九十一隻。沒死的動物,逃跑了,不知所終。被打死的,還算新鮮的話,紅軍士兵拿去做了烤肉晚餐。
英國在一九三九年九月三日正式對德宣戰,備戰措施卻早在一年前就已經開始。預估德軍的轟炸和毒氣攻擊會造成大量傷亡,宣戰前就已經準備了三十萬具棺木,並且拆下街道欄杆做了六十萬具鐵擔架。鐵擔架在戰後發現剩下太多,於是又重新裝回去做欄杆,到現在,倫敦還有好幾條街的欄杆是鐵擔架的原型。
戰爭爆發,動物園第一個動作當然就是處死危險的動物。珍稀動物就疏散到郊區動物園。除此之外,政府擔心一旦開戰,糧食開始配給,那麼士兵的糧食優先,平民的糧食會嚴重缺乏,不能夠讓貓狗寵物分掉戰時存糧,於是發「備戰傳單」給全國人民:儘速把你的貓狗送去鄉下,不然就想法處死他們。
傳單上有一把「擊昏槍」的圖片。擊昏槍的使用方法是,把槍口抵住動物的前額,扣扳機,「子彈」射出後其實會重新彈回槍膛內,沒有火藥,但是打擊的強度可以讓動物瞬間腦死。
傳單上還特別註明:「擊昏槍,任何體型大小的狗都可以用,也適用於牛」。
✽
傳單一發布,英國的獸醫診所門前大排長龍,人們帶著自己寵愛的貓狗來「安樂死」,一周之內就有七十五萬隻貓狗被殺。九月三日宣戰後,更大量的貓狗被「處理」掉。(註二)
抱著貓、牽著狗來「處死」的人,或許流著眼淚,心如刀割,可是,戰爭本身是個一旦啟動你無法輕易叫停的機器。
而且戰爭,從來沒有停止過。烏克蘭本來是歐洲大陸的野生動物大本營。俄烏戰爭的兩年中,國際的動物保護組織不間歇地想方設法拯救動物園裡頭的老虎、獅子、黑豹、熊。但是烏克蘭百分之二十的生態保護區已經成為戰區,估計有六百多種珍貴動物和七百多種植物直接受戰火威脅。二○二二開戰以來,烏克蘭森林大火已經超過一千次,地雷和砲火直接點燃了森林之外,森林的地面布滿了黑色的火藥殘餘和砲彈碎片。
沙灘下面埋進了無數的地雷,加上海裡的戰艦聲納不斷發出音波,已經使得大海也變成戰地,不久前,上千隻海豚被發現死在黑海的海灘上。(註三)
✽
我的動物專車搖搖晃晃進入了深山。新開出的公路打通了一座山,隧道完成,從西岸到東岸節省了半個小時。開車的人,在山的肚子裡行駛,出了隧道就看見從前只有野獸和猛禽看得見的新鮮風景。山如此之綠,樹如此之密,嶄新的、乾淨的路,如此的齊整,像一把新鑄的劍。
這段山路貼著懸崖而走。路上突然出現兩隻動物,跟狗差不多大。緊急煞車使得輪胎發出刺耳的摩擦聲,車內的貓籠、狗籠、雞籠猛地往前衝,一陣雞飛狗跳,受驚的母雞嘎嘎大叫,在籠子裡猛拍翅膀。
以為是白鼻心,細看之下,原來是兩隻長尾穿山甲,一大一小,就在山路中間。小心停下車,走出車外看仔細些。這對穿山甲,相互依靠著,似乎是母子。穿山甲通常夜間行動,現在接近中午,怎麼會出來覓食?難道是因為,公路鑿山開洞、砍伐森林,打通了山脈,也將他們原來的棲地切割,阻斷了他們自由覓食的通道?或是穿山甲的森林腹地不夠了,不得不離開森林來找吃的?
更奇怪的是,穿山甲是最容易受驚嚇的動物,他們尤其躲著人類,登山的人想看到他們都不容易,怎麼會在光天化日之下的路上停下來?
山風徐徐,滿山的樹木搖晃,細雨已止。在朵朵雲團飛行的節奏裡,陽光在雲間閃爍,天空時不時露出一小塊晴朗的藍。穿山甲顯然是從我左手邊的森林裡鑽出來的,正在往路右邊的懸崖峭壁前進。走到懸崖邊往下看,嚇一跳,山崩的裂石碎礫如瀑布一樣傾入山谷,鋼筋做成的網,把上半段的土石固定。這顯然是一個常常坍方的地點。
山谷很寬,一條溪蜿蜒於中,正是冬天枯水期,河床乾涸,裸露的鵝卵石閃閃發光。
兩個一身盔甲的動物朝向我觀望了一下,開始移動。小的穿山甲把兩隻前腳搭在媽媽的背上,緊緊貼著母親,幾乎是讓媽媽拖著前行,完全像個拉著媽媽裙角撒嬌的小孩,但是小穿山甲一瘸一瘸的──是不是受了傷?
母子相偕走到懸崖邊,消失的那一刻,我才發現,小穿山甲的尾巴斷了半截。
他們的鱗片在陽光的照射下,閃著金黃色的光。
後來獸醫告訴我,穿山甲尾巴多半是被咬斷的。過去可能是被獵人放進森林裡的金屬捕獸夾把尾巴夾斷,現在大多數卻是被遊蕩犬撕咬斷裂的。
人,把捕獸夾埋置在森林裡,讓野生動物斷腿斷腳。人,把狗帶到山林裡丟棄,讓狗飢寒交迫,然後變成山裡飢不擇食的遊蕩犬猛獸。森林裡小型的野生動物突然發現自己處在隨時可能被野狗包圍撕裂的環境裡。
繼續前行,經過一個又一個的原住民部落。這條人以為傲的穿山公路,把人帶到夢想的遠方。開路之前,山裡的原住民背著竹簍,負著沉重的產品,下山去交易,是一趟無比艱辛的行旅,幾天幾夜的攀登和跋涉之外,還包含一路毒蛇猛獸的威脅。現在,山中生活的人輕鬆了,外面世界的人,如我,也進來了。開山開路,通暢便捷,改變了原住民的生活,擴大了我的視野和世界,同時也毀了「非人類動物」的生存環境。
而這一切,都是回不去的了。
✽
貓不停地喵喵叫,車子的行駛對他們真是不可理解的天搖地動。小狗則天真酣睡,把車當搖籃。上車時在台灣海峽,一覺醒來已是太平洋。
抵達新家,第一個先快快抱下貓籠,把飽受驚嚇的他們帶進屋內,貓需要室內的安全感。
然後抱下狗籠,放在草地上,打開門。兩團肉球伸展一下身軀,跳上綠油油的草坪,開始打滾。
雞籠一打開,所有的雞歡快地拍著翅膀,像放學的小孩,迫不及待連飛帶跳地衝出。對她們而言,眼前是無邊無際的青草,青草裡必定是有肥美的蚯蚓。
唯有芝麻,趴在那兒不動,圓圓的黑眼睛盯著我看。她想說什麼?
伸手把芝麻抱起來,看見她趴著的草墊,被她的體重壓得淺淺凹下,有一顆雪白渾圓的蛋。摸一下,溫溫熱熱的。
抱起暖呼呼的芝麻,我低頭親吻她粉紅色的雞冠。
(本文選自時報出版龍應台新作《注視──都蘭野書》)
註一:羅家倫,《逝者如斯集》,商務印書館,北京,二○一五,頁23-24。
註二:https://reurl.cc/rvOqeE
註三:https://reurl.cc/Kl1WGR
加入 琅琅悅讀 Google News 按下追蹤,精選好文不漏接!
逛書店
猜你喜歡
贊助廣告
商品推薦
udn討論區
- 張貼文章或下標籤,不得有違法或侵害他人權益之言論,違者應自負法律責任。
- 對於明知不實或過度情緒謾罵之言論,經網友檢舉或本網站發現,聯合新聞網有權逕予刪除文章、停權或解除會員資格。不同意上述規範者,請勿張貼文章。
- 對於無意義、與本文無關、明知不實、謾罵之標籤,聯合新聞網有權逕予刪除標籤、停權或解除會員資格。不同意上述規範者,請勿下標籤。
- 凡「暱稱」涉及謾罵、髒話穢言、侵害他人權利,聯合新聞網有權逕予刪除發言文章、停權或解除會員資格。不同意上述規範者,請勿張貼文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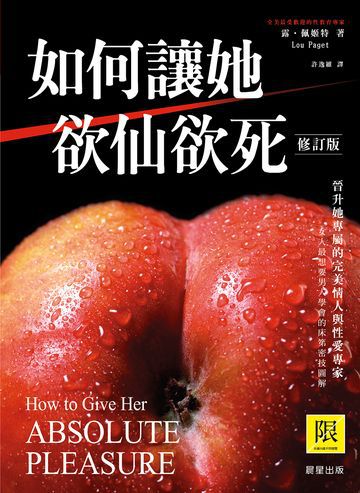






FB留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