蕭詒徽/魔王與奴隸(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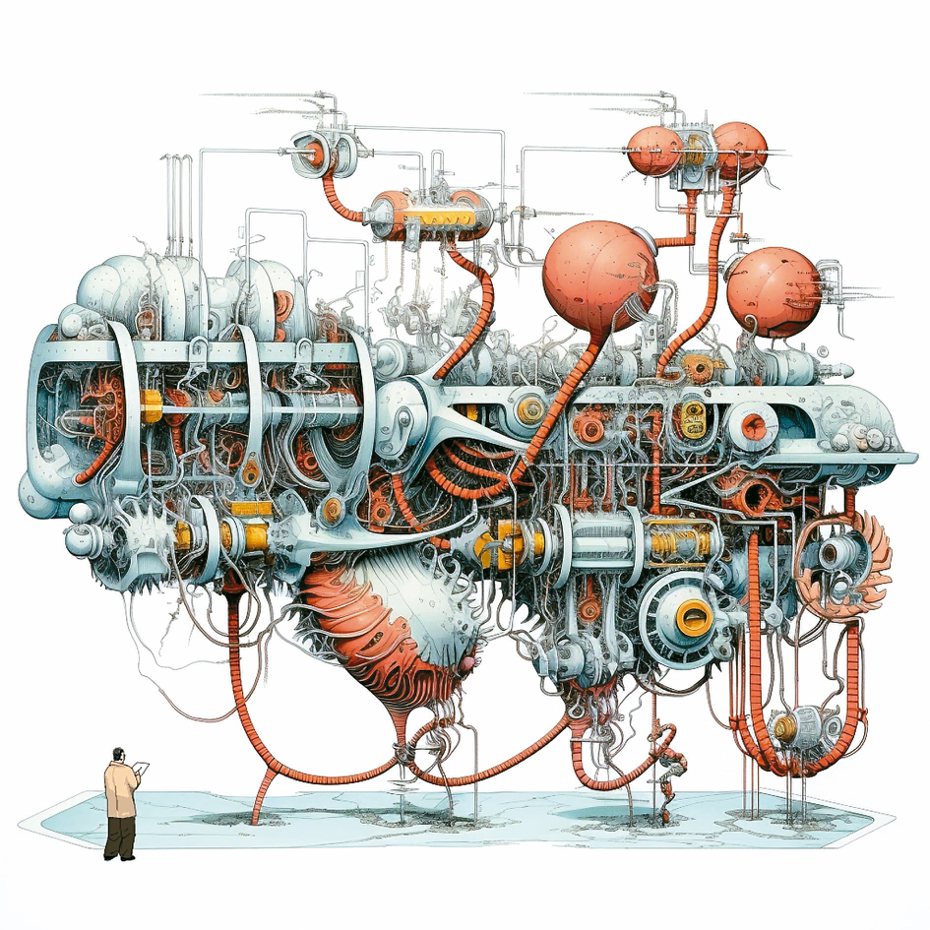
1.
我的第一份影集劇本工作,恰好開始於台灣觀眾開始大量訂閱Netflix的2018年。那時還沒有HBO GO,沒有Disney+,Netflix這個詞在人們的對話中幾乎等於串流本身,就像Google自動轉品為線上搜尋的動詞。而就像Google的壯大連帶創造了SEO等搜尋引擎優化技術的興起,形成一整套提高網站搜索排名的策略,N家的崛起也並不只是讓世界多了一句「Netflix & Chill」而已。
我們的編劇統籌乃賴,某天開會時興沖沖地分享了一件事:
逛書店
「你們知道,Netflix上的平均上鉤(hooked)集數是第四集嗎?」
Google「平均上鉤集數」,點開排名第一的搜尋結果,裡頭是這麼解釋的:「Netflix蒐集超過六十部節目的全球觀影數據,發現70%的觀眾看了節目中某集就會一路追完整季,換句話說,也就是『引人上鉤的關鍵一集』讓觀眾一追就『回不去了』。」
真正令乃賴興致高昂的應該不只是上述發現本身,還包含了這個發現所顛覆的舊觀念:傳統電視影集通常將第一集視為最重要的集數,然而Netflix從數據中發現根本沒有觀眾在第一集就上鉤。
「意思是,我們有更多時間鋪陳故事的開頭,」乃賴說,「如果觀眾願意看完三、四集才決定要不要棄,我們不必急著在第一集丟出那麼多東西。」
2.
那時也還沒有AI;或者說,沒有人想到AI將在幾年後成長到足以成為好萊塢編劇罷工的理由之一。但乃賴分享這個觀察的情景,已經帶有一點數據與創作交互聯繫的影子了——企業以大數據歸納了一個結論,而創作者根據那個結論調整自己的心與手,連帶使這個世上影集的敘事線有所變化——而AI和大數據之間的差別,略嫌簡單地說,也不過就是多了「是否依據數據再行輸出」這一步。
如今回想,那時決定將第一幕hook安插範圍從一集延長為三集的我們,就是依據資料數據走出那一步的人。我們是資料數據和AI之差的那塊人肉零件。
讓坐在編劇會議室裡的我感到矛盾的是,從一集到三集的這件事既是一種解放,同時我們也都明白它很快就會成為一道新的束縛——稍微碰過編劇的人都曉得,由於產業合作模式多工化以及資金量級的龐大,編劇就算不是第一、也是第二最講求定型化結構的文字工作了。你一定聽過Pamela Douglas的名著《超棒電視影集這樣寫》中如何用A-B-C故事與兩頁場次方法構築影集劇本;如果和電影比較靠近,可能也會對美國編劇Blake Snyder所創的Blake Snyder's Beat Sheet略知一二。偶爾,編劇們甚至會照著這些表格填入關於不同角色的上百個戲劇節拍。
Netflix的發現及其影響,不過是這個龐大系統的一次階段性調整而已。
我是這個系統末端的一個小小編劇。說不曾有過被體制宰制的虛無感是不可能的。我好奇自己到底要早出生多少年、至少可能要讓我的編劇生涯早過Pamela Douglas出那本書的2005年,才能讓我不受種種規則的約束自由地創作劇本?
然後,我發現我可能至少得早出生個一百年才夠。
3.
1931年,數學家哥德爾為了證明數學的不完備性而創造哥德爾數:他為每個數學含義建構符號,例如「非(~)」、「如果……那麼(⊃)」或者大家熟知的「等於(=)」。這個符號系統,讓每一個用語言表達的數學命題,都可以用符號表示。
接著,哥德爾將這些符號各以一個正整數代表;當一個數學命題用上述符號系統表達時,它同時也形成一個正整數序列。這個序列可以拿來依照哥德爾的方式編碼,作為第n個質數的指數並相乘,使得每一個命題都可以是一個不與其他命題重複的數字。
總之,在哥德爾的編碼下,「0乘以X等於0」這個命題,可以寫成這個數:
2⁶×3¹²×5¹³×7⁵×11⁶
而比哥德爾早三年,俄羅斯作家Vladimir Propp發表了一本奇書《民間故事形態學》(Morphology of the Folktale)。這本書整理了俄羅斯的民謠和抒情歌曲,還有俄羅斯農民的節慶。Propp在分析這些故事時,認為它們全部總共只有31個基本元素;他替這些元素編號:1. 離去/2. 禁令/3. 違反禁令……而這些元素在故事中發揮了什麼「功能」則被賦予了其他符號(例如α、β、A、B)。
總之,在Propp的書裡,有一個沙皇與三個女兒與惡龍搏鬥的故事被寫成這樣:
β³δ¹A¹B¹C↑H¹-I¹K⁴↓w°
想不到吧?當人們想像寫作的人數學不好,一世紀前的民間故事分析式比數學還難懂。
4.
Propp並不是唯一一個嘗試將文學創作以某種方式解剖成運算規律的人。
再晚個三年,美國作家Wycliffe Hill開始了他命名為「情節精靈」(Plot Genie)的工具書系列。書中,他和Propp一樣將角色、情節等故事元素編號,然後告訴讀者只要使用另售的數字輪盤,不必等待靈感、只要轉一轉,五分鐘就可以生產一個故事。
1944年,英國作家Henrietta Rosa Montague又發明了「姓名選擇器」。這個手掌大的機器由兩個輪軸構成,軸上列有各種名字,只要隨機轉動,就不用花時間想名字了。
這些宣言,是不是像極了如今ChatGPT等一眾大型語言模型的口號?
跳回2022年。第一次合作四年後,我竟再一次有緣和乃賴合作一檔影集開發。不同的是,這時ChatGPT與相關應用開始在大眾普及,編劇和其他文字工作者開始生活在一個巨大預言的籠罩之下:你們要被AI取代了。
妙的是,與作家末日的陰霾一同被應許的,是只要有心就可以藉由AI生產無限作品的奶與蜜——AI一I(人)分飾兩角,既是終極的魔王,又是現成的奴隸。
這一次,我們要寫的故事有關都市傳說:其中一集,主角因為課業壓力,找到帶有魔力的「第十三個書架」許願,讓自己擁有高超的應考技巧,代價是讓書架上的書蠹寄生肉體……
六個月了,劇本寫作陷入瓶頸。乃賴仍是那個乃賴,擅於用工具和理智解決問題。某天他和導演請我們讀《韓國影劇故事結構聖經》中的一章,要我們找出角色在敘事線上來自敵對力量的三個攻擊點——以經典情節三角布局/敵對者或困境/高潮為結構,找到主角行動的起點與終點——
故事依舊沒有進展。
Propp的符號分析和Hill的情節精靈,這種思路自然也有它們的敵對力量。更精確地說,它們才是那一股應對世界的反作用力:在這些方法出現前,十八世紀的人們認為「創作者的才華」是一種看不見的力量,無法透過學習、模仿或實踐來獲得。然而,到了十九世紀,我們開始看到不同的說法:
「也許作家們不願以真實的創作過程破壞他們浪漫的形象。」愛倫坡在《作品的哲學》中寫道,「但獨創性不僅僅是一種『衝動或直覺』,而是戰略性工作的回報。」
「我自己的詩〈烏鴉〉並非是一道受到啟發的狂熱,而是在一步一步進行之下,才得到的寶貴而嚴格的結果,猶如數學問題。」
才華究竟是一種神祕的天賦,還是可以被分析、破解的東西?在「情節精靈」和「才華」之間,永恆的拉鋸——至今這個問題的幽魂尚未離開,只是它們有了各式各樣的變形:「創作可不可以教」、「文學線上課有用嗎」。而它最新的一種形態正是:
「AI又沒有心,怎麼可能創作出真正動人的作品?」
5.
而這些看似靈魂叩問的難題,竟然也投射在科技發展的進程之中。二十世紀中,當人們開始將情節精靈式的工具放進電腦,試圖創造比手轉輪盤更偉大(也更有用)的生成機器,有人認為它們神奇,有人拒絕全然信任。1960年,一款名為「ELIZA」的程式藉由分析心理治療中個案話語裡的關鍵詞,生成相應的回應。資料記載,當時ELIZA和個案進行了以下對話:
個案:男人都一樣。
ELIZA:在哪方面?
個案:他們總是糾纏我們,問東問西。
ELIZA:妳能舉一個例子嗎?
個案:嗯,就是我男朋友把我逼到這來的。
ELIZA:妳男朋友讓你來這裡?
個案:他說我大部分時間都很沮喪。
ELIZA:聽到妳感到沮喪,我感到抱歉。
然而,ELISA的開發者Joseph Weizenbaum,在報告中卻用一種極似AI時代人類的說詞,又是警告又是自我安慰地寫:「我們不應該將一次功能性的成功,與能深層思考的智能模型混淆;ELIZA可能模擬了治療師和患者之間的對話,但並沒有捕捉到心理醫師如何理解愛的經歷。」
呃,愛?
我有許多解決劇本卡關的方法,其中一個是找別人聊天。某晚,我和前同事互傳訊息,前同事告訴我她最近加了某鮮肉演員的LINE官帳。「那個帳號會傳『晚安』、會傳『下班妳餓了嗎』,還會叫我早點睡覺。」前同事說,「好療癒,好暈。」
「可是,那應該不是鮮肉本人吧。應該是小編吧。」劇本寫不好的時候,我就想傷害別人。
「可是,他怎麼會知道我什麼時候下班?這難道不是一種天啟嗎?」
Weizenbaum的提醒,在我前同事美好的心靈中踢到鐵板:你如何分辨功能性的成功和深層思考呢,假如對方光是收到回應就已經足夠,並且從中獲得填滿?(上)
加入 琅琅悅讀 Google News 按下追蹤,精選好文不漏接!
猜你喜歡
贊助廣告
商品推薦
udn討論區
- 張貼文章或下標籤,不得有違法或侵害他人權益之言論,違者應自負法律責任。
- 對於明知不實或過度情緒謾罵之言論,經網友檢舉或本網站發現,聯合新聞網有權逕予刪除文章、停權或解除會員資格。不同意上述規範者,請勿張貼文章。
- 對於無意義、與本文無關、明知不實、謾罵之標籤,聯合新聞網有權逕予刪除標籤、停權或解除會員資格。不同意上述規範者,請勿下標籤。
- 凡「暱稱」涉及謾罵、髒話穢言、侵害他人權利,聯合新聞網有權逕予刪除發言文章、停權或解除會員資格。不同意上述規範者,請勿張貼文章。







FB留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