蔣勳/懷念,摩羯小黑(上)

2010年12月16日,因為突發性心肌梗塞,在台大急診。裝了兩支支架,在加護病房觀察四天。
出院後做復健,醫生諄諄囑咐每天要運動,走兩萬步。
我原本就愛走路。在紐約或巴黎,常常從早走到入夜,大街小巷,一座一座的橋,一區一區的森林,可以隨時坐下來享受一下風景,看一段書,或者發呆。
有一段時間喜歡住布魯克林區,早上就穿過布魯克林大橋,大河浩蕩,二十世紀迎接工業初期的工程,延續著岩石結構的古典,又蠢蠢欲動,有著鋼鐵世紀來臨的生命躍動。
從橋上遠眺曼哈頓島的繁華,繁華讓人浩嘆,彷彿只是一夢江山。
這樣閱讀一個城市,比閱讀一本書真實。
穿過中央公園,秋天的落葉紛飛,一路踩著落葉走到公園大道,走到古金漢美術館,不覺已是黃昏。
一個城市,這樣沒有目的,從早走到晚,就有驚人的文化能量吧。
巴黎是青年時流浪的地方,沿著塞納河,從東一直往西走去。跨過一道一道的橋,很簡單的Pond des Arts,左邊是法蘭西學術院,右手邊是羅浮宮,東邊是聖路易島,四百年前最早的「新橋」,西邊是標誌城市進入二十世紀的艾菲爾鐵塔。
從左岸走到右岸,再從右岸走到左岸。巴黎需要在河流的兩岸穿梭,步行,像縫紉織繡,把一個城市最古老也最珍貴的記憶縫在自己貼身的內衣裡。
那時候母親擔心出外遇到扒手,在我的貼身內衣親手縫製一個口袋,可以密藏重要證件或錢。
那個口袋裡裝著我青春時的巴黎,在貼身的胸口,有著心跳的微溫和悸動。不用看,不用打開,就知道那美麗的城市一直在那裡,你會不會去,她都在,不離不棄。
米哈波橋其實比亞歷山大橋要優雅得多。2024奧運開幕太誇張,亞歷山大橋的金碧輝煌,那座迎接俄皇駕臨的大橋,都是壯偉雕像,金光閃閃,帝國沒落前不可一世的炫耀誇張。
阿波里奈爾,凝視二十世紀初的工業旭光,凝視從帝國衰退裡再度重生的城市。任何角落都可以仰望艾菲爾鐵塔,米哈波橋下流水波紋,手與手的牽繫,擺脫了財大氣粗的擺闊張揚,新的城市市民愉悅歡快,步履輕盈,走上米哈波橋。
可以一直走到布隆尼公園,前一晚城市慾望氾濫,森林樹叢,到處遺落保險套、女人的絲襪、大麻菸蒂……
從高雅到低俗的慾望,都看到了,恰好穿過一個城市由東往西的軸線。
「軸線」是文化的傳遞延續,許多宏遠視野的執政者提起巴黎的「軸線」。從路易十四羅浮宮前的雕像,通過協和廣場,穿過香榭里舍大道,穿過凱旋門,一直到La Défense,巴黎最西的端景,迎接二十一世紀的「大拱門」。
我想念巴黎嗎?好像也沒有,她一直在貼身的口袋,緊靠胸口,沒有離開過。
會離開的城市,大多沒有可以慢慢走路的行人位置。
所以,我居住的城市是很難走路的。
國際媒體上說「行人地獄」。
有人憤世嫉俗,插著腰回覆:「就是『行人地獄』,怎樣!」
「OK啊……這麼兇……」街頭吵架,也讓行人怵目驚心。
我謹記著醫生的囑咐,每天兩萬步。從出院開始,認真執行,一大早用過早餐就沿著河邊從南往北走。
這條河流,早期有許多垃圾漂流下來,有床墊、沙發,各式鞋子、衣服、帽子,會浮起來的胸罩,藍白拖鞋。有動物屍體,有漂流木。一頭死豬的腫脹屍體,在河邊盤旋幾日,腐爛了,爬滿招潮蟹,發出惡臭。
我記憶著那時的河流,彷彿上游仇恨著下游,「要你好看」,最後一整條河都臭爛不堪,難以靠近。
住在臨河四樓,窗台上看風景,忽然就看到一包垃圾飛躍而過,落在河裡。附近造船工廠,油漆也直接排放入河,河水一時藍,一時綠,一時紅,像是魔幻電影。
四十年前在對岸一所大學建築系教課,談到這條河流,「河流如果上下游彼此仇恨,也是行人地獄」。我那時不太敢靠近河邊,惡臭會窒息而死。
教室裡有一位學生,轉讀水利工程,畢業後進了水利署一類機構服務。他偶然寫信給我,說:「每一天都在努力讓這條河流改變。」
我很想謝謝他,和他的同僚,因為他們「每一天」的努力,家門口的垃圾少了,臭味減少,小工廠不隨便排放汙水,河水變清澈了,有了步道,河岸邊水筆仔紅樹林茂密生長,散步的人多起來了。
一條河流,下游終於可以感謝上游,彼此不再仇恨。
2010年的冬天我可以安心在河邊步道走兩萬步了。
記得是一月十日左右,我剛過了陽曆生日。照常出外兩萬步,過了冬至,河邊東北季風加強,頂著風走,把頭臉包好,帽子、圍巾、外套、厚毛襪,讓自己保暖。
出門不久,經過小土地廟,再往前,三十分鐘,有一處石雕工廠,配合大眾庭院設計,會有仿維納斯石雕、愛神石雕,也有地藏菩薩手拿禪杖,旁邊坐著「善聽」。
「善聽」據說是神獸,虎頭,犀角,有狗耳,成為地藏座騎。地藏發宏願,要去地獄救度眾生。「地獄不空,誓不成佛。」這樣的誓願,使人心痛,要如何達成啊……幸好有「善聽」一路陪伴,牠的靈敏狗耳聽到受苦呻吟,便帶地藏前往,這樣一頭善盡職責的動物,也讓人動心。「要不要養一頭?」「不要,不要!」心裡有一個聲音立刻拒絕,拒絕這麼快,什麼原因?
一百年來,河流的上游、中游,流過城市最繁華的地區,艋舺,西門町。繁華總是同時產生大量垃圾。上游壅塞了,發展到中游,大稻埕、大龍峒,河邊都是南北貨商鋪,黃金買賣熱絡,酒家也林立。不多久,一樣淤塞,船隻不到,要靠新興鐵路取代。
我的童年在大龍峒,同安人建立商業繁盛的四十四坎,猶然是四十四層樓分類井然的百貨公司。
然而,河流邊林投樹林,懸掛和漂流的,都是貓狗的身體。
也許童年就認清城市的繁華背後有這麼多寵物屍體腐爛著……
遷居到下游出海口附近,常常南面而望,「上游,上游,你會帶給我什麼?」
那時候這一帶叫作「台北縣」,包圍著繁華城市的蛋黃,這個叫作「縣」的廣大地區,是初來城市打工的人聚集地,三重、蘆洲、五股、板橋、新莊、中和……房價低,許多簡陋工廠,出外打拚,艱難求活。大橋頭邊,一大早看到三重青年工人坐在路邊,等候老闆吆喝點名,工人便爬上貨車,算著一日工錢多少。
一直住在城市邊緣,看到的景象,不只是繁華,也是城市努力生存者的另一種況味。
下游最初來的人不多,有了關渡大橋之後,遊客多了,地價漲起來,一棟一棟蓋起大樓,城市中心居民,很容易驅車,把不要的垃圾帶到「偏遠地區」丟棄,包括棄養的寵物。
寵物,也是城市繁華的景象。都市中心昂貴地段,一個十字路口,四個角落都是寵物醫院。
二十一世紀之後,上游漂流下來的廢棄物少了,從大橋驅車來的大包垃圾和寵物多起來了。
住在下游,觀看上游,一直有一種仰望,羨慕,同時也懼怕,「可以不要用自私傲慢對待下游嗎?」下游的人只好這樣祈求。
寵物遺棄是一種最難面對的「垃圾」。有名種的哈士奇、貴賓狗、秋田、柴犬……
為什麼被遺棄?
頸上還留著頸圈,頸圈有的很講究,粉紅色皮質,兩個金色心型扣環,掐著被遺棄的沮喪的脖子,看到異常心痛。
心痛,不只是寵物被如此對待,也是那兩顆金色的心型,彷彿回憶曾經有過的一段愛情?愛情結束,怨毒太深,連寵物也一起憎恨。
拋棄到河邊時,頭也不回,聽得到那寵物哀哀嚶嚶哭泣嗎?
我走在成為「新北市」的下游左岸,愉快的心情常常被這些上游遺棄寵物的嚶嚶哭泣弄到哀傷不已。
繁華必然是這樣無情糟蹋生命的嗎?
但是,我無助無奈,不知如何解決。這些數量龐大的遺棄寵物,好像一整個城市繁華的虛妄幻相,使下游仰望上游時,如看待繽紛煙花,也有一個接一個心型圖像,節日原來如此,寵愛可以瞬間成為垃圾。
寵愛瞬間成為垃圾,我們還可以安心在此時的愛與安逸中嗎?
河邊的步道像修行的路,有許多黃槿,清晨鮮豔,午後就都萎落在地上。有一座小小土地公廟,附近有住戶每日上香供養水果,也有謀殺案,兩具屍體隨潮水流回來,擱淺在廟旁,像是向神明告訴。
修行的路上,公部門提醒大眾:「陸蟹經過,小心慢行」,雖然還是看到有碾碎的蟹的小小身體。
草叢裡有冇骨消,開碎碎白花,受傷的狗知道前去咀嚼。
如果是天生在河邊流浪的貓犬,大抵沒有那麼讓人感覺到悲哀,雖然生存艱難,看到人類,有時狺狺,露出白牙,但大多夾尾逃竄,消失在河邊許多藏身洞穴。
寵物一旦受寵,再被遺棄,連狺狺的本能也沒有。想靠近人,搖尾乞憐,又害怕被凌虐,在親近與恐懼的尷尬矛盾間,眼神閃爍,惶惶度日。
羸瘦皮包骨,皮膚生瘡,動作不敏感,常被快速車輛壓傷,拖著一條腿躲在草叢裡,驚慌看走過行人。
修行的路上,有許多「不忍」,難以釋懷生命要受這樣折磨。然而那「不忍」一無所用,對受苦者一無助益。《金剛經》最讓我震動的句子是「實無一眾生得滅度」,修行的路上,要對自己的「不忍」,棄如敝屣,連頭都不可以回嗎?
於是,我遇到了要回頭的時刻,便默默警告自己:「實無一眾生得滅度。」
如果回頭了,將是什麼樣的因果?
讓我回頭的是如今已經消逝十年的「小黑」,我要說牠的故事嗎?
那是2011年的一月,我開始每天兩萬步不久。有東北季風來,河面一片寒霧,平日常見的遺棄寵物也躲藏起來,空曠的河岸邊,那座石雕工廠散置在各處的維納斯與地藏菩薩都各安其分。「善聽」似乎也聽著嘶嘶寒風,辨別方向。
我聽到草叢裡嚶嚶的哭聲,立刻告訴自己「不要回頭……」
很稚嫩的幼犬的哭聲,不只一隻,我繼續跟自己說「不要回頭」。
然後,我回頭了,循聲到河岸坡坎石塊的間隙,看到兩隻蠕動的小狗,一條純黑,一隻間雜棕色的紋路。
生命無辜,總不知道為何要來世間受苦。
我蹲下去看他們,撫摸牠們。牠們舔吮手指,很用力,那樣渴望活下去,抬頭看,寒冷河邊,看不到可以照顧的母犬,「母親呢?」不是應該有母親嗎?
我是有母親照顧的寵兒,覺得母親照顧天經地義。
被寵壞的生命才有天經地義的狂妄傲慢吧……
眾生裡,落地的黃槿,碾碎的陸蟹,遺棄的寵物,都比我知道「沒有天經地義」。
「天經地義」的狂妄傲慢,只是還不識因果吧……
當你回頭了,當你蹲下去,當你撫摸,當你被舔吮手指,你會情不自禁叫出聲「小黑」。
我研究動物的朋友說,解剖室的青蛙、老鼠都不准命名,一旦有了名字,就下不了手。
可是,我叫了牠「小黑」。
我帶牛奶去餵食,牠們飛快長大。「摩羯座,小黑──」牠俊挺漂亮,春天來的時候,坐在我面前,好神氣自在,讓我羨慕牠的端正相貌。
加入 琅琅悅讀 Google News 按下追蹤,精選好文不漏接!延伸閱讀:蔣勳/懷念,摩羯小黑(下)
逛書店
猜你喜歡
贊助廣告
商品推薦
udn討論區
- 張貼文章或下標籤,不得有違法或侵害他人權益之言論,違者應自負法律責任。
- 對於明知不實或過度情緒謾罵之言論,經網友檢舉或本網站發現,聯合新聞網有權逕予刪除文章、停權或解除會員資格。不同意上述規範者,請勿張貼文章。
- 對於無意義、與本文無關、明知不實、謾罵之標籤,聯合新聞網有權逕予刪除標籤、停權或解除會員資格。不同意上述規範者,請勿下標籤。
- 凡「暱稱」涉及謾罵、髒話穢言、侵害他人權利,聯合新聞網有權逕予刪除發言文章、停權或解除會員資格。不同意上述規範者,請勿張貼文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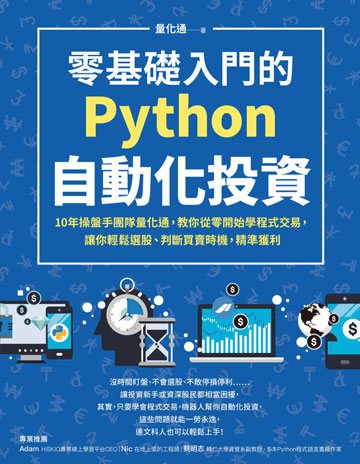




FB留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