龍應台/認識自己的來時路——《野火集》序2023

今天二十歲的人讀一九八五年的《野火集》,可能會覺得,他所知道的台灣,不是「那樣」的啊。
一九八五年「那樣」的台灣,任何入口處都擠成一團,人們不習慣排隊,排隊經常有人插隊;受傷的人躺在馬路中間,會沒有人停車相助;一路噴黑煙的汽車滿街跑,打電話到環保局不會有人處理;行車遇糾紛時,對方可能拿著扁鑽下車朝你走來;淡水河裡到處是漂浮的垃圾;住宅區裡違規的工廠鎮日轟轟作響;海邊燒廢棄電纜,產生的毒素使得鄰村嬰兒出生缺少大腦;工廠廢料大股大股流進溪水海水;市民到任何公家機關辦事都要受公務員的頤指氣使;國外進口的雜誌標題被塗黑;美術館的作品因為被告密有「紅色」嫌疑而被竄改;公開演講是一件令人擔心身家性命的事情……
今天的台灣,在國際旅客的普遍印象中,是一個文質彬彬、友善又熱情的社會。生態保護的意識極高,公民素養的程度整齊,經濟發展的模式可敬,政治自由的進程更是一個標竿。
在寒流來襲一個冬日,坐在忠孝東路大道旁一張長椅,一縷陽光突然破雲而出,就那麼一大束強光照在步履從容的台北人頭上,那麼亮、那麼暖。
我有突如其來的泫然欲泣的感覺:這一份陽光中的淡定和從容──如果你認得那一路走來的足跡,知道其中有多少人一代又一代的努力和付出──是多麼、多麼的不容易,多麼、多麼的珍貴。
認識自己的來時路,人看世事或許就比較寬厚。當台灣人斥罵或譏笑其他地區的人們不排隊、隨地吐痰、亂丟垃圾、蠻橫粗魯的時候,我不會附和,因為,走過從前,知道自己曾經如何地踉蹌艱難,同理心會超越優越感。
一九八五年二十歲的人,三十八年後重讀《野火》,心境或許深沉、複雜許多。
台灣比起從前,可愛太多了,然而,一九八五年說過的話,三十八年後,社會質變如此之深,是不是不必再說了呢?
好像又不是。
所以我很怕談「愛國」,因為我知道當群眾對「愛國」認起真來而至狂熱的時候,這個「國」就成為一頂大帽子,要壓死許多不那麼狂熱的個人。要談愛國,我寧可一個人上山撿垃圾。(〈難局〉)
那時的「國」,是「中國」,台灣代表「自由中國」。一九八五年雖然距離解嚴只有兩年,但是沒有人可以預見隧道盡頭有光,那仍是個恐懼噤聲的年代。不「愛國」,是可以招來大禍的。
到了二○二三,你以為在開放社會裡,政治是一種自由的個人抉擇。但並非如此,只是這時的「國」,變成「台灣」,「愛台灣」成為道德制高點。
不得已,今天仍舊要說:
所以我很怕談「愛台灣」,因為我知道當群眾對「愛台灣」認起真來而至狂熱的時候,這個「台灣」就成為一頂大帽子,要壓死許多不那麼狂熱的個人。要談愛台灣,我寧可一個人上山撿垃圾。
一九八五年還不流行「媽寶」這個詞,但是〈幼稚園大學〉批評大學的校長和師長把大學生視為幼兒:
學生怯懦畏縮,是他們缺乏勇氣,還是我們迷信自己的權威,又缺乏自信,不敢給他們挑戰的機會?
辦教育的人,或許本著善意與愛心,仍舊習慣地、固執地,把大學生當「自己的兒女」看待,假定他們是被動的、怠惰的、依賴的。這個假定或許沒錯,可是教育者應對的方式,不是毅然決然地「斷奶」,而是繼續地呵護與控制,造成一種可怕的惡性循環……
把我們的大學生當「成人」看吧!給他們一個機會,不要牽著他的手。(〈幼稚園大學〉)
三十八年過去了,台灣的山不全面開放,台灣的海不全面開放,因為,都是危險的地方,不要去。不僅只是政府認為他有權利和義務「呵護」人民,人民一般也認為自己應該被政府「呵護」。
不得已,今天仍舊要說:
把我們的人民當「成人」看吧:給他們一個機會,不要牽著他的手。
一九八五、八六年,「台灣意識」是一個禁忌詞,與「台獨」幾乎要畫上等號。因此在整個「野火」期間唯一的一次演講,題目是「我的台灣意識」,我這個演講者和台下以及廳外伸長了脖子的聽眾,整場都處在一種神經緊繃的不安中。
……要建立台灣意識,首先,教科書必須全面地改寫。告訴下一代台灣不「僅只」是個復興基地,她也是個有歷史、有文化、有長久的未來,需要細心經營的「家」。歷史老師不只告訴孩子們玄武門事變與黃花崗七十二烈士,還要帶著小學生去看卑南遺物,走草嶺古道。地理老師不只告訴孩子們青海高原的氣候如何,更重要的是領孩子們坐阿里山的小火車,觀察在哪一個氣候帶有哪一種植物。講解宗教時,老師不僅只談書本上的儒道釋,他還要帶孩子們到廟裡去,在香煙裊裊中告訴孩子們媽祖、土地公、七爺八爺、城隍爺,究竟是怎麼回事。
「台灣意識」要這樣從根植起,讓它慢慢發芽、長大,在台灣這塊土地上生活的人──沒有外省本省的分別──才可能建立起有特色、有實質的受全體認同的文化。(〈我的台灣意識〉)
三十八年中,「台灣意識」已經成為理所當然的「正統」,教科書更是全面改寫了。這,就是《野火集》當年的願景嗎?
不全是。渾厚的文化從來不會建立在排他性強、唯我獨尊的基礎上。三十八年來台灣意識的茁長相當程度被一種窄化了的意識型態挾持,「非我族類」被視為「他者」,真正的融合認同難以達成。
不得已,今天仍舊要說:
「台灣意識」要這樣從根植起,讓它慢慢發芽、長大,在台灣這塊土地上生活的人──沒有外省本省的分別──才可能建立起有特色、有實質的受全體認同的文化。
一九八五年,用「飼料」這個詞來比喻國民黨對思想的操弄,當然是帶刺的。
在一個言論受到操縱控制的社會裡,選民的知識就像飼料管中灌輸下來的豬食,是強餵的,而且只有那麼一種。既然沒有多種思想飼料讓他自己做選擇,他就從來沒有機會學習如何去辨別品味,識別良劣。(〈歐威爾的台灣?〉)
民主制度裡,這種話,不必說了吧?不可思議的是,民主了之後,執政者對思想的操弄,譬如媒體的收買及控制,手段更複雜、行徑更誇張、企圖更大膽。尤其當執政者更有能力的時候,它利用科技可以全面地滲透、掌控,而且,因為是軟性手法,人民還不覺得被矇,欺騙性比威權時代還有過之。
不得已,今天仍舊要說:
在一個言論受到操縱控制的社會裡,選民的知識就像飼料管中灌輸下來的豬食,是強餵的,而且只有那麼一種。既然沒有多種思想飼料讓他自己做選擇,他就從來沒有機會學習如何去辨別品味,識別良劣。
一九八五年,反共是最高的國家政策,防止敵人滲透和維護國家安全是穩定社會的基本原則。為了「安定」,所有的控制都可以合理化。《野火集》描述科學家如何把一群老鼠聚集到一個平台,面對兩個門,往下跳,右邊的門一碰就會鼻青眼腫,左邊的門一碰就開,裡面出現好吃的乳酪。老鼠經過多次錯誤之後終於弄清了情況,學會了往乳酪門跳。一旦形成習慣,實驗者就把乳酪換到另一個門去。等到老鼠多次再度鼻青眼腫之後學到了新的教訓,適應了新的情況,乳酪又換了地方。
這時,老鼠就出現一種精神崩潰症狀。他無法適應新的情況。
一個國家,又何嘗不是個精神可能崩潰的老鼠?國際局勢的變化多端就好像乳酪的忽而在左、忽而在右。三十年前解決問題的方法不見得能解決二十年後的問題。如何能不受制於舊習慣、舊觀念、舊方法,如何不搞「擰」了去老撞一扇沒有乳酪的門而撞得鼻青眼腫,需要的是彈性和智慧。(〈精神崩潰的老鼠〉)
那是一九八五年對威權執政者說的話。
二○二三年,對民主制度下的執政者,還有必要說嗎?
認識自己的來時路,使我們更清醒,記住歷史的是非不被統治術矇騙;使我們更感恩,珍惜自己所努力獲得的一點一滴;使我們更謙卑,明白相互的體諒與扶持,路可以走得更遠。
(本文為《野火集》傳奇經典版序文,近日將由時報文化出版)
加入 琅琅悅讀 Google News 按下追蹤,精選好文不漏接!逛書店
猜你喜歡
贊助廣告
商品推薦
udn討論區
- 張貼文章或下標籤,不得有違法或侵害他人權益之言論,違者應自負法律責任。
- 對於明知不實或過度情緒謾罵之言論,經網友檢舉或本網站發現,聯合新聞網有權逕予刪除文章、停權或解除會員資格。不同意上述規範者,請勿張貼文章。
- 對於無意義、與本文無關、明知不實、謾罵之標籤,聯合新聞網有權逕予刪除標籤、停權或解除會員資格。不同意上述規範者,請勿下標籤。
- 凡「暱稱」涉及謾罵、髒話穢言、侵害他人權利,聯合新聞網有權逕予刪除發言文章、停權或解除會員資格。不同意上述規範者,請勿張貼文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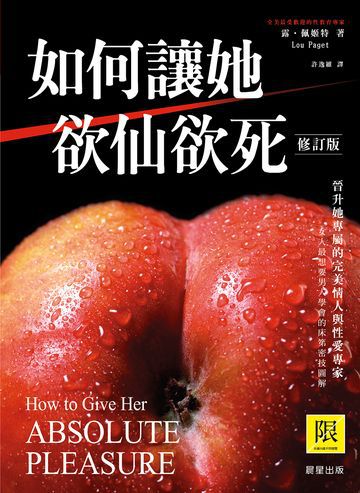







FB留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