鄧依涵/過年的地方

讓同姓氏的家人聚在一起的夜晚
每年到了這個時間,叫做過年。對大部分的人來說,有過年得做的事,該去的地方。集中在這段時間裡所經歷的事情,彷彿是木材切面在乾冷季節生長減緩而形成的深色輪紋。每年,時鐘繞過兩回三百六十五圈,那一棵種植了家的模樣與自我印象輝映的大樹,經過一年四季的深淺交替,又長出一層新的年輪。
過年與家與家人與我的意義,都與時間繫在一起。
小時候,過年的地方不是「家」,是除夕夜跟大年初一的「阿嬤家」,或是,偶爾初二會去的「外公外婆家」。那時候我住在鄰近宜蘭市西邊的員山鄉,雖然門上掛的門牌地址是員山鄉,隔著一大片田,對面馬路就是宜蘭市了。學校也在宜蘭市。住在宜蘭的親戚,平常經常在阿嬤家相聚,我和姊姊從學校放學,也走路回阿嬤家等媽媽來接。
阿嬤家是近的,阿嬤卻常常擔心我和家裡不夠親。不像姊姊是被阿嬤帶大的,我出生後,媽媽把我送到住在阿嬤家對面的奶媽家,奶媽與阿嬤的年紀相仿,我用發音不標準的臭奶呆叫她婆婆。小時候我對婆婆的依附極深,阿嬤不只放在心裡,也會掛在嘴上:「依涵在我們家怎麼像外人一樣,吃什麼東西都要問,好像變成阿寶她們陳家的小孩……」
於是,當我嚷著要去奶媽家過年,簡直觸動了究竟我是誰家的小孩的地雷,媽媽受不了問我:「妳那麼愛婆婆,妳到底是我生的還是婆婆生的?」尚未習得生殖知識的我,遇到了一個大難題,發育中的腦容量有限,絞盡腦汁,說出了我當下認為的正解:「我一半是媽媽生的、一半是婆婆生的!」
因為有了過年這樣特別的日子,我學習到,原來對大人來說,除夕的團圓,是讓同樣姓氏的家人們聚在一起的夜晚,就像冠上爺爺姓氏的阿嬤,阿嬤生的兒子與他們再生的、與我同輩的堂兄弟姊妹,我們都姓鄧。媽媽與嬸嬸就跟阿嬤一樣嫁進了鄧家,成為「鄧家人」。姑姑、姑丈與表妹一家,平日經常在阿嬤家一起吃飯、出遊,唯獨除夕與初一缺席,也是這個道理。至於婆婆,屬於只要過了除夕夜之後,都是可以去拜訪的「別人家」。我不曉得這是誰定出來的規矩,問大人,大人也回答不出來。只說,就是這樣。
最靠近圓心的那幾圈年輪,要怎麼過年,可沒有我置喙的分。就連試著從嘴邊溜出一句疑惑:「那,爸爸也姓鄧,為什麼爸爸過年不在家?」想了想,就乾脆不問了,反正也得不到真正的答案。
我用一張紅色跟他換了兩張藍色
爸爸在外地工作很長一段時間,先是在台北,後來又去了其他地方。從間隔幾個月就會帶禮物回家一趟,到後來,過年也不見得會回家。過年的年輪,也分成了爸爸在的一層,與爸爸不在的一層。
當爸爸不在的過年,我和姊姊便愁眉苦臉。真正原因跟爸爸在或不在,其實沒有太大關係,而是到了初二這天,我和姊姊換上新衣滿心期待要和外公外婆拜年,媽媽就會說,爸爸又不在,我不會開車,蘇澳太遠了。我們可以搭火車去啊?或是,我們去找住在宜蘭的舅舅,請舅舅載我們一起過去?
也許媽媽不回娘家的真正原因,超出了當時小小年紀可以理解的範圍,但我跟姊姊怎麼管得著,每年外公外婆都會給我們超大包紅包,因為爸爸不在家,這個新年損失慘重。
幸好,無論爸爸在不在,在阿嬤家的除夕夜,一定會從阿嬤和叔叔嬸嬸們的手上,拿到好幾包壓歲錢,當作那年的本金。阿嬤家的廚房流理台底下總是疊滿了碗盤,在眾多碗盤之中,有一個碗公似乎用透明的馬克筆寫上「十八骰仔專用」,平常大家養成了默契,在阿嬤家開伙時都不會用到這個碗公,只在除夕夜這晚孩子們一拿完紅包,就看誰搶頭香衝到流理台底下,搬開上方堆疊的碗盤,抱著碗公端到客廳桌上,成了最有人氣的一道年夜菜。
記得有一年,手氣特別不好,壓歲錢都快輸光了,嘟著嘴要哭了出來。沒想到,比我小幾歲的堂弟,也一樣氣噗噗的表情,可他手上明明捧著從其他兄弟姊妹贏來的一大疊紅包。弟弟帶著欣羨的眼神,跑過來小聲問我,可不可以跟我「換」,他喜歡紅色、不喜歡藍色。我看著他紅包袋裡滿滿的藍色千元大鈔,再看向自己輸到只剩下紅色的百元零鈔,趕緊把他帶到無人的二樓,進行這場祕密交易。我說,可是我紅色的也沒剩幾張了,但既然他那麼想要,不然,我用一張紅色跟他換兩張藍色。弟弟開心點頭,把我所有的百元鈔都換走了。於是那一年最後,小賺小賺。
爸爸再三重述那份縝密的通告單
長大後,過年的地方變成了「家鄉」。升上大學之後到台北讀書,離開宜蘭,就再也沒有回去住了。在我北漂的日子裡,從小到大印象中總是在外地工作的爸爸,也漂回了台灣。爸爸在新北市,我在台北市,過年到了,我們會一起回宜蘭。
「我六點起床,從這邊六點半出發,七點到妳那邊接妳,八點到宜蘭,十點拜拜,十二點開飯……」過年前一周,每天都會接到同樣內容的電話,爸爸再三重述這份縝密的「通告單」。不知道是怕別人忘記還是怕自己忘記,連他起床時間都要講給我聽。
除夕一早,爸爸的車七點準時出現在租屋處樓下。穿過雪山隧道,八點到宜蘭崇聖街市場採買新鮮魚肉蔬果。以前住在宜蘭的時候,很少踏進傳統市場,更別說是這種年味沸騰、人氣旺盛的除夕版本。
爸爸腳步飛快卻從容不迫,原來除了給我的時間通告,宜蘭傳統市場裡的哪一條巷弄、哪一格攤販,爸爸心裡也有一份完整的食譜地圖。我跟著爸爸的背影,穿過市場裡熙來攘往的人潮,側身俐落地閃開挑菜殺價、緩慢滑行的機車,還有早早把菜賣完、開心收攤回家過年的攤販推車。
我從爸爸手上,接過一袋又一袋的塑膠袋,從康樂路走進北館市場的麻醬麵攤前,領了號碼牌等座位。一旦空閒下來,爸爸又想到了還缺什麼,逕自往市場棚架的另一側鑽去,不一會兒就拎著兩大袋古早味白粉圓回來。吃著宜蘭特有的道地麻醬麵與餛飩湯,這一份家鄉味,中午以後就收攤了,可想而知也在爸爸安排的通告行程裡頭,帶著我一同回味。
提到我爸,我經常用一些方式介紹他。其中,只要講起我家的年夜飯是我爸煮的,每個朋友的反應幾乎都同等驚訝,帶著笑意瞪大眼睛:「真的假的?你爸會煮年夜飯?」
姑姑說,我爸做菜的手藝是偷學來的。以前家裡環境很不好,有飯吃就不錯了,即便每頓飯都吃一樣的也不敢嫌。我爸作為家中的大哥,每當遇到婚喪喜慶路邊出現辦桌菜的總鋪師,就會鑽到棚子底下觀察那些師傅是怎麼料理食材的,回家自己試著照做給弟弟妹妹吃,調整火候跟調味,久而久之,什麼菜都做得出來。
小時候,對於爸爸在家過年的印象十分稀薄。長大以後,每次看到他在除夕這天捲起袖子、煮滿一大桌年夜菜,我才意識到,這些忙碌的身影,或許不只是為了這個晚上的一頓飯,更像是他用一圈一圈的年輪,把過去缺席的時光補回來,把作為大哥的責任和對家人的重視親手端上桌。
這或許是我該習慣思考的事情了
直到去年,爸爸不再只是家裡的大哥,總算如願以償,當阿公了。孫子在哪兒就成了爸爸過年的地方。往年對過年一家人團聚有種種堅持的老爸,終於拋下他萬年不變的通告單,跑去美國幫姊姊帶孩子,滿心歡喜含飴弄孫。但一想到過年,爸爸依然不放心地拿起手機,一通一通電話聯繫,深怕大家沒有他煮的年夜飯,這個年就不知道怎麼過了。結果,叔叔們得知爸爸過年會在美國顧孫,也訂了機票趁春節出國旅遊,反倒剩我和媽媽留在台灣。
我問媽媽過年想怎麼過,媽媽說看我。那還要回宜蘭嗎?還是就留在台北?媽媽一樣說,看我。那一句「看我」,第一次聽到的感覺有些陌生,甚至覺得「怎麼會是看我咧」。但後來想想,這或許是我該習慣思考的事情了。
原來過年的方式,終究會變成一道選擇題,一份精心的責任。沒有夫家、沒有妻家,也不需要回老家了,沒有不得不遵守的習俗,記憶的年輪自然留住了歷年刻畫的過年篇章,未來的日子要怎麼過年,其實,早就種下了生長的方向。
我跟媽媽說,不如今年就在我台北的租屋處過年,我來煮年夜飯給她吃。「妳會煮?」怎麼可能,我又沒煮過。「可是……總要有個人開始學著煮年夜飯。」所以,就讓我來煮煮看吧。
加入 琅琅悅讀 Google News 按下追蹤,精選好文不漏接!逛書店
猜你喜歡
贊助廣告
商品推薦
udn討論區
- 張貼文章或下標籤,不得有違法或侵害他人權益之言論,違者應自負法律責任。
- 對於明知不實或過度情緒謾罵之言論,經網友檢舉或本網站發現,聯合新聞網有權逕予刪除文章、停權或解除會員資格。不同意上述規範者,請勿張貼文章。
- 對於無意義、與本文無關、明知不實、謾罵之標籤,聯合新聞網有權逕予刪除標籤、停權或解除會員資格。不同意上述規範者,請勿下標籤。
- 凡「暱稱」涉及謾罵、髒話穢言、侵害他人權利,聯合新聞網有權逕予刪除發言文章、停權或解除會員資格。不同意上述規範者,請勿張貼文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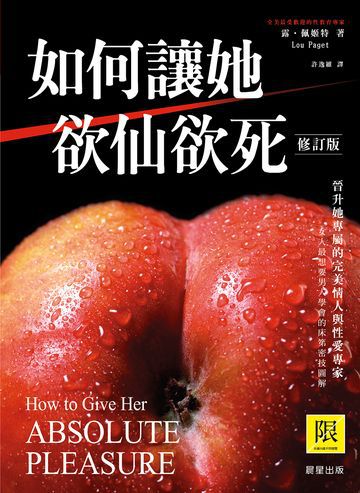




FB留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