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懷民 /吶喊與突圍──薪傳45(上)

一九七八春天,我在洛克菲勒三世基金會的獎助下到紐約遊學,住進五十八街的小公寓。幾條街外就是哈德遜河,偏僻,荒涼。薄牆外車聲人聲聲聲入耳,爛床廁浴小廚房加上我的行李箱,幾乎不能動彈。沒到布魯克林或皇后區租屋,只因我出國前演出意外的腳傷未癒,保險給付的復健師在西五十七街。
深夜,我不時被摔破酒瓶和罵街的聲音吵醒。每天早上,上班族急促的腳步聲是我的鬧鐘。往往未吃早餐,我就出門,到街角買《紐約時報》。美中關係日益密切,中國表演藝術團就要到林肯中心演出。臺美關係崩裂只在旦夕。我困坐陋室,無力,想家,想自己怎麼流落到這個牢籠裡。
那時,我沒想到,鄉愁可以是一齣舞劇的種子。
少年時讀舊俄小說,夢想將來也寫厚厚的家族小說。紐約遙想嘉義新港,才發現自己對林家的事知道得很少,兜起來,也許只能寫個三五千字。
我想念在臺灣的舞者。
我們是叛逆的孩子,跳出社會就業的正途,跑去跳舞。雲門草創的年代,學舞的孩子交學費,花錢做服裝,演出時銷票,沒聽說跳舞可以賺錢。
舞蹈系畢業的何惠楨、鄭淑姬、吳秀蓮、吳素君、王雲幼,應該去開舞蹈補習班,存錢,準備嫁人。淑姬每天撒不同的謊,瞞著母親到雲門排舞。惠楨排完舞,就睡在排練場的小房間。
舞者只有在年度演出後才能分到一些酬勞。平日,有人去藝工隊上班,有人應邀去教幾堂課。晚上的工作,不接,那是到排練場上課,排舞的時段。收入青黃不接的時候,有人減餐,餓著肚子跳舞。我知道後,把政大的薪水放在一個架子上,讓需要的人拿去用。沒有人去碰那些錢。大家都鬱卒,卻無人開口,怕壞了士氣,只有舞動時才能忘卻現實的困難。

一九七八年,我在美國,舞者自己給課,自己編舞,在吳靜吉、樊曼儂的協助下,到南部演出。沒有手機,沒有傳真,我不知他們好不好,演出是否順利……
坐著發悶沒道理,起來做點有前途的事吧。五十七街表演經紀公司林立,我拿著一頁雲門簡介,兩張照片的文件夾去敲一家一家經紀公司的門。祕書說老闆不在,有的客氣的要我留下資料。一位經紀人從紙堆抬起頭來,看了看簡介,撕出一個笑容:「我們再聯絡。」
唯一能做的,我想,就是回去編一個讓舞者開心的舞,希望演得好,賺到錢,讓大家不那麼捉襟見肘。
夜晚,看著掉漆的天花板,我模模糊糊的記起長輩們說過,新港人的先祖是在笨港大水後,護著天后宮的媽祖神像,遷移居較高的麻園寮。他們建造廟宇,供奉媽祖。麻園寮發展成新港小鎮,媽祖廟就是今天香火鼎盛的奉天宮。小時候,我常爬上廟口的石獅上玩,有時就趴在獅頭上睡著了。我想,也許可以編一個舞,關於逃難,護著媽祖神像。
八月底,我回到臺灣,發現雲門在高雄演出,趕緊飛下去看。時差的我看到臺上的舞者和滿場自己人的觀眾,恍如隔世。
然而,我不知那個舞長得什麼樣子。
有學者說,解嚴後,臺灣研究從「險學」變成「顯學」。一九七八年,我想知道顏思齊和笨港十寨的事,重慶南路書店巡了幾回,關於臺灣的書,只找到薄薄一本林衡道先生的《臺灣歷史百講》。讀完後,我想,應該往洪水前推,講先民帶著媽祖神像渡海到臺灣,以及登陸後的拓荒。
我去新店找雲門的創作顧問奚淞聊。他總是溫暖的鼓勵人,立刻說:「柴船渡黑水,唐山過臺灣。很好呀!」我講得興奮,仍然不知舞該怎麼跳,望向窗外,綠浪的稻田外就是新店溪。我們到河邊走了一趟。溪水汪汪,有些地方開著薑花。
我時差纏綿,舞者忙了幾個月,排練,演出,累了。周末大家一起到新店溪郊遊吧。
到了溪畔,舞者傻了眼。九月天,日頭炎炎,岸邊岩石磊磊。我很尷尬,就說,我們躺下來休息吧。頭部、背後都是石頭,如何休息?有趣的是,不去想它,身體自動放鬆,大家竟然睡著了。陸續醒來後,我建議大家翻身,貼著石頭河床爬行,再慢慢站起來走動。石灘高高低低不好走,走著走著,身體自動調適,放低了重心,不再舉步維艱。那麼,走快一點,然後,跑跑看。找到重心就不會跌倒。

我對大家說,從地上爬,站起來,走路到跑步,那就是祖先移民臺灣的歷程。好像胸有成竹。
我們繼續到河邊「郊遊」。小睡,走路,跑步,然後搬石頭。小的一個人搬,大的兩三人合作。搬得順手後,練習拋石頭,重點是接到時,身體一定要更沉,要把石頭「收到肚子裡」。接拋時把肚子裡的氣吼出來,野地有多遼闊,聲音就得那麼長。
黃昏,大家圍坐岩石堆成的小丘閉眼休息。雲門的音樂指導樊曼儂誘導舞者隨著吐納發聲,再把自己投入和諧的聲流裡,集體把聲音往上推,到了最高潮再緩緩收聲。野地休息的即興吟唱日後成為《薪傳》的序幕,在開演前安定舞者和匆忙到場的觀眾的心情。
然後分享心得。所有人都提到重心的運用:愈沉重的石頭,重心要愈低。在新店河邊,我們找到排練場不容易達成的低重心體態。那是農民勞動的體態。先民是農民。
我也請舞者講自己的家族史,許多人必須回家問父母或祖父母,才瞭解長輩走過的路。幾乎所有的家庭都經過艱苦打拚的歲月,而且仍在奮鬥。
我們決定用這個舞向祖先致敬。舞作以上香開啟,把香插到香爐後,舞者脫下時裝,化身先民,展開〈唐山〉、〈渡海〉、〈拓荒〉、〈播種/豐收〉與〈節慶〉的歷程。
關心雲門的張繼高先生約我到家裡喝茶,問我在美國看了些什麼,問我回來要做什麼。我說在籌畫一個新作,要點香向祖先致敬,舞題就叫「香火」。張先生說構想好極了,「香火」有點俗氣,不如叫「薪傳」。張先生又笑嘻嘻地說:「沒有白吃的午餐,版權費一塊錢。」我欣喜地掏出一個銅板:「成交!」
誰也想不到,「薪盡火傳」,出自《莊子‧養生主》的兩個字,竟會隨著舞作的演出,變成社會日常用語。
我興致勃勃地訂製一塊大白布,準備「渡海」。像許多舞團,雲門男丁不足,一艘船,一定要有舵手,還要有兩名舞者抬起一個壯丁當桅手,一下子去了四位男生。我煩惱不已。師大體育系畢業的洪丁財說動兩位學弟加入雲門。精瘦黧黑的蕭柏榆和鄧玉麟到新店河邊報到,在烈陽中走近,彷彿來了兩位農民。
兩個人是體操高手,會翻能蹦,都沒學過舞。《薪傳》的動作語彙因此找到準繩:阿蕭阿麟不會做的芭蕾轉圈圈之類的展技統統掃地出門,留下的是質樸的,低重心的身體,騰躍奔馳。
兩個人個頭都不高大。阿蕭篤定,阿麟輕巧,剛好是舵手和桅手的最佳人選。南京東路巷子裡,公寓的四樓,屋頂很低,兩名男舞者肩膀上的桅手站起來頭碰梁柱,排練時只能坐著扯起象徵風帆的白布。我們翻飛大白布變化景觀,發展出辭鄉,揚帆,狂濤巨浪,媽祖靖海,抵達臺灣的結構。就這樣,我們用兩三次的排練,完成了〈渡海〉。從未編得如此迅速,後來也不曾如此順手。
葉台竹與吳素君當了爸爸媽媽。坐完月子的素君到了新店河畔,不能搬石頭,只能看別人練功,同時知道自己無法參加演出。
我看著她孤坐的身影,決定在〈拓荒〉裡加添一個角色,讓有生產經驗的素君演出孕婦,夫婿意外身亡後生下遺腹子。〈渡海〉的白布可以成為喪禮的裹屍布和遮掩生產的簾幔,簾後飛出血流般的紅綢,產婦抱住在島嶼誕生的第一個嬰兒,堅毅地踩著血路向前邁進。
不少人問我《薪傳》的女性為什麼那麼強悍。拓荒必須強悍。為母則強。真實的理由也許是舞者中,有幾位是客家人:何惠楨、劉紹爐、王連枝,還有阿蕭。素君和阿麟是半個客家人。他們把客家精神帶進《薪傳》。
苗栗來的何惠楨吃苦耐勞,個性倔強,成為〈唐山〉中堅持要為後代前程渡海離鄉的母親,抱著嬰兒,篤定踩地,每一步都像要把地板踩出洞來。
連枝的母親會洋裁,我請她複製美濃的客家服裝。男舞者光上身,黑、藍褲子,比較簡單。女子藍衫、黑衫,大襟縫上欄干,開衩高,前襬可以反摺,塞到腰上,便於勞動。舞蹈服裝,因為不斷舞動,往往不講究細節,王媽媽說這樣不好,把幾十個盤釦也照規矩一一縫製。
舞者穿上王媽媽的作品,紮起頭髮,皮膚抹黑,活生生是先民的形貌。這批首演的服裝穿了二三十年,從舞臺退休後,一直珍藏在雲門服裝組。
然而,我沒有音樂。
雲門從七三年草創以來,始終用本土作曲家作品編舞。我出國期間,音樂家也為舞者的創作譜曲。《薪傳》來得突然,編舞的人不知它會長成什麼樣子,說不出所以然,十二月要首演,委託長曲來不及了。
我找出紐約帶回來的「鬼太鼓」的唱片,選出一首鼓樂,打發了〈渡海〉,又把新店練就的發聲與動作結合起來。曲膝勞動時嘿嘿吐氣,海上掙扎時尖聲哀叫,拓荒時長長的呼號,暗示土地的遼闊。我決定了,要用有節奏的人聲,腳步聲,貫穿全劇。
九月,十月,雲門南北奔波演出。我們用零碎的時間,繼續到新店溪畔練習,也在排練場編出片片段段的舞句。十月底,高雄演完,整團人開赴滿洲佳洛水,在海瀑的岸邊,用呼吼對抗不斷撲來的浪潮。
首演訂好十二月十九日,國父紀念館。到了十一月,我們還在嘿喔嘿喔,太乾。從創團時就擔任舞團音樂指導的大毛──樊曼儂,我每次喊救命的時候,總是伸出援手。看到我又擱淺,便把急躁心慌的我按坐下來開會。
既然〈渡海〉用了鼓聲,大毛說那就繼續用打擊樂。她找來許婷雅,以及二十二歲的「天才兒童」陳揚來救場,用打擊樂來撐起沒有音樂的〈唐山〉、〈拓荒〉,以及最終的〈節慶〉。
後來改名婷雅的許壽美出身新竹名醫的家庭,一九六六年與阿美族音樂家李泰祥私奔成婚的消息成為報紙頭條。這段浪漫的戀情最終以離婚收場。婷雅二◯◯八年往生。
那幾年,我編舞有嚴重的文字障,務必說清楚講明白。我想到陳達。希望他能用〈思想起〉的曲調講述先民渡海拓殖臺灣的故事,作為舞段中的間奏。
十一月底,邱坤良慷慨仗義,遠赴屏東,轉恆春,把七十四歲的陳達帶到臺北。
進了錄音室,老先生問:「沒酒怎麼唱?」幾口米酒,幾粒花生米後,陳達撥彈月琴,滔滔不絕即興開唱,從「祖先鹹心啊要過臺灣」起,唱了三個多小時。我說,可以了。老先生答道:「還沒唱蔣經國呀。」唱完蔣經國和十大建設,陳達陡然以「臺灣後來好所在,三百年後人人知」漂亮作結。我們這些年輕人震驚得呆住了。
臺灣,臺灣,我發現《薪傳》可能是第一齣以臺灣歷史為主題的劇場作品。一個恐怖的發現。
威權時代,審查制度橫行。審查人員想像力豐富。賴德和等年輕音樂家組「向日葵樂會」,沒通過,因為向日葵把頭歪向「東方紅」。
一九七七年,鄉土文學論戰,書寫本土故事的寫實作品被官方文人批評:是工農兵文學,過度強調臺灣意識,有主張臺灣獨立的嫌疑。中壢事件後,情勢益加嚴峻。甩一頂「臺獨」的帽子給《薪傳》不是不可能。
有記者聽說雲門在編先民開臺歷史的舞劇,跑到南京東路排練場,希望跟我聊一聊。那陣子,吳靜吉常來坐鎮,打氣,好說歹說才勸走記者。南渡墾殖是史實,但我怕媒體的報導會引來警備總部或文工會的關心:蠻橫的禁演,或客氣地要你「想一想」。
我決定把首演搬到顏思齊墓的所在地,嘉義,向開臺先民致敬──遠離警總,即使事後被禁演,至少演完一場。
當時我不知道,這個匆促的決定,會嚴重影響雲門日後的發展。(上)
加入 琅琅悅讀 Google News 按下追蹤,精選好文不漏接!逛書店
猜你喜歡
贊助廣告
商品推薦
udn討論區
- 張貼文章或下標籤,不得有違法或侵害他人權益之言論,違者應自負法律責任。
- 對於明知不實或過度情緒謾罵之言論,經網友檢舉或本網站發現,聯合新聞網有權逕予刪除文章、停權或解除會員資格。不同意上述規範者,請勿張貼文章。
- 對於無意義、與本文無關、明知不實、謾罵之標籤,聯合新聞網有權逕予刪除標籤、停權或解除會員資格。不同意上述規範者,請勿下標籤。
- 凡「暱稱」涉及謾罵、髒話穢言、侵害他人權利,聯合新聞網有權逕予刪除發言文章、停權或解除會員資格。不同意上述規範者,請勿張貼文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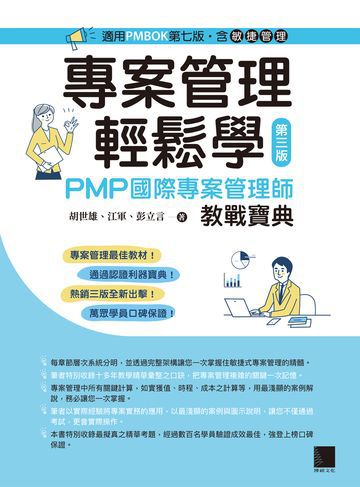



FB留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