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舉報我說毛澤東萬歲」白恐受難者病危 仍記掛冤獄戳記

文.圖片提供︱ Liglav A-Wu(利格拉樂·阿𡠄)(排灣族散文作家)
無法返家的靈魂
初見黃勳東前輩
坐在狹長的客廳裡,我聽著一旁的臥室中,女子低聲地以阿美族語詢問著床上躺著的病人,一陣安靜沒有回應,只有沉重的呼吸聲緩慢地傳出,不過短短的幾秒鐘流淌,我卻如坐針氈的感覺到前所未有的漫長。
經過了病人的同意,我進入那窄小的臥室中,除了一張單人床之外,最多只能再添兩、三張椅子,臥床正對著鐵窗,屋外有些許午後的陽光偷溜進來,鐵條圖樣的線條映照在對戶的水泥牆上,隨著秒針的聲音,一點一點地逝去了痕跡。望向躺在床上的老人,雙頰已經明顯的消瘦,卻顯現出病態的嫣紅,蒼白的雙脣隱隱地顫動著,唯獨那一雙眼睛炯炯有神,矍鑠的不像剛剛從急診室搶救回來的臨危病人。他是黃勳東前輩,臺東縣關山鎮電光部落的阿美族人,原住民族名叫做Kacaw Tomum(卡造.東門)。
我找到前輩的當日上午,他剛剛因為大腸癌併發症,才從附近的醫院急救緩和下來,初抵達家門安置好,我後腳跟著就前往造訪,明知道這個時間不適宜,卻意外地獲得家屬的同意,於是狠下了心進門訪問。會如此心急的叨擾,實在是因為尋找前輩的過程過於艱困,檔案資料中記載的是1972年前輩遭到逮捕時的戶籍所在地地址,我循著線索找到電光部落的時候,才從前輩的大妹口中得知,他早已遷居到桃園中壢,許久不曾回到部落了。


部落入口處其中一幢老式的平房面對著馬路,隔著一條產業道路就是清澈的水圳,放眼望去滿是綿延到山腳下的翠綠農田,大妹打開緊鎖的老家大門,微微的煙塵撲面而來,不至於瞇眼卻嗆了呼吸道,淺淺的咳了幾聲後,她手指了左側的房間,「那是哥哥以前住的房間。」沒有房門,門楣上掛著已然褪色的紅色花布,掀開門簾看去,除了少數雜物外,最顯眼的是遭到蟲蟻蛀蝕的梁柱和木床架。
回到大廳, 正中間是祭祀祖先牌位的神龕,兩側的牆上掛滿家中成員的個人照或大合照,我在一張明顯是家族齊聚的大照片下站定,大妹指了指最後排左側的位置,微有不滿的噘著嘴說:「那就是大哥。」這是我第一次將檔案資料中的黃勳東前輩和本人疊合。
來自家人的誤解
「大哥坐牢的時候,我去探過一次監,那時候我在社子島的紡織工廠。」1960年左右,大量的原住民離開部落前往都市工作,前輩的大妹也趕上了這波出走風,阿美族人多數不是往北走到工地從事板模工,或進入大型工廠當第一線的工人,就是往南走到高雄港口,成為了遠洋漁工。
站在屋外的庭院裡,身為長女的她,對於這個備受父母寵愛的哥哥有著情緒。當年父母努力耕種賣稻,自己進入沒日沒夜的紡織工廠,傾盡全家之力送大哥遠赴屏東內埔農工讀書,那一年部落只有兩個青年考取外地學校,能夠遠離部落繼續深造,沒想到幾年後卻得來哥哥遭到關抓的消息,母親甚至在大哥被捕失去音訊後,曾經前往高雄找尋他的下落未果。在她的理解裡,大哥是做錯了事情才會入獄,這個印記讓留在部落裡的家人受到異樣的眼光盡是煎熬,幾年之後,母親也因為抑鬱成疾溘然長逝。
臨離開老家前,她遞來小妹的電話,表示小妹與大哥較有聯繫,也聽說了大哥近年身體狀況不佳,也許找到小妹就能找到大哥,並沒有表現出其他多餘的情緒,之後默默地將老家大門上鎖,騎著摩托車頭也不回的離開了。我站立在水圳旁,手握著她給予的紙片,想起無法向前輩的家人解釋他是遭遇冤獄之事,竟是久久無法平息感傷。
後來的幾個月裡,我試圖撥打紙片上的電話,只是始終沒有人接聽,找尋黃勳東前輩一事突然就陷入了困境,直到某日心血來潮,帶著不死心的蠻勁,再度撥打出那個電話,卻意外地接通了。電話那端正是前輩的小妹,她只是淡淡地說著:「你可能要盡快,大哥的時間不多了。」這才知道原來前輩罹患大腸癌已經三年,近日已多次在急診室搶救,未免遺憾,當下我就和小妹約定了隔日拜訪。三月乍暖還寒,氣溫高高低低的起伏著,有時白日還艷陽高照,入夜後溫度便直線下降,變化的讓人不知所措。在小妹的引領下,我們爬上位於小公寓的三樓,沒有陽光照射的客廳裡,寒氣有些冷冽,覆蓋在暖被下的前輩,因為又和死神奮戰了一次,蒼白而疲憊的神色讓人有些不捨;我的內心裡劇烈的掙扎著,一方面不忍心在這種情況下做訪談,卻又更擔心隨時會失去一位受難者當事人的記憶,最終,只能撇去心思啟動訪談,而正如我所憂慮的,這是我與前輩在他離世前唯一一次完整對話。

前輩於屏東內埔農工畢業後,認為西部比較有工作機會,因此前往高雄前鎮加工區,對應60年代起始的都市原住民潮,不難理解他為何選擇了這個地方,因為這裡是南部最容易遇到族人的區域。高中畢業的學歷讓前輩不用跑遠洋,因為他擁有留在陸地上工作的優勢,當時的高雄前鎮加工區正逢臺灣經濟起飛時期,大量的工人湧入,也創造更多的生活機能需求,於是前輩進入了由加工區所經營的餐廳。
成立於1966年的前鎮加工出口區,是全球第一個加工出口園區,面積與規模之龐大可想而知,光是園區內所附設的餐廳就有九間,依照消費能力的客群,分別從一號餐廳編號到九號餐廳。前輩在1970年左右來到前鎮,投入了最基層的九號餐廳,每日從揉饅頭、送各工廠的便當開始做起。「我還記得那兩個年輕人,高中畢業的呢,在餐廳裡面打雜,後來人就不見了。」我很意外地在前鎮加工區四號餐廳,找到了當年與前輩同事的大廚,他對具有高中學歷卻到加工區打雜的兩人印象深刻,一位是客家籍的鍾德富,另一位正是原民身分的黃勳東。
為什麼會被抓呢?「有人舉報我說毛澤東萬歲。」虛弱的前輩談起當初被逮捕的原因,眼神緊緊地凝視著我,毫不猶豫的給出答案。對照加工區的大廚敘述,事情發生在1972年的中秋節,餐廳裡的員工聚集在一起吃飯看電視,那時候老三台也才剛剛建置完成,節目大多與政令宣導有關,他並不知道現場黃勳東到底說了什麼,只知道隔天兩個高中生都不見了,因為族群身分特別,格外引發他的關注,事後才理清是有外省籍的退伍軍人到警察局內的保防單位檢舉。
顛沛流離的一生

那一年,黃勳東剛滿二十歲,正值人生開啟的黃金時期,因為一個莫名的舉報,他先是被警察帶走訊問,然後移送到臺北警總景美看守所(今白色恐怖景美紀念園區),經過三個多月的羈押,最終被判處有期徒刑四年,罪名是「連續以演說為有利於叛徒之宣傳罪」,後來因為蔣中正過世減刑,最終服刑兩年八個月(檔案紀錄);「我在新店被關了兩年七個月。」儘管事情已經過了將近五十年,他依然記憶清晰,不經思考的就答了出來,一旁的妻子微微蹙了眉頭,滿臉的疑問與困惑,這是她第一次聽到丈夫說出被關的細節。
屋外的光影已經徹底消失了蹤影,微寒的風透過窗櫺的隙縫鑽進房間,前輩喘著氣,明顯的有些不舒適,我在心底暗暗決定要結束這次的訪談時,他突然又開口說道:「他們歧視原住民和客家人,我們都是被陷害的!」類似哮喘的咳嗽聲陣陣傳來,前輩似乎仍堅持著想說些什麼,最後在家屬的勸阻下,才緩緩閉上眼睛陷入沉眠。
「哥哥出獄的前一天, 有警察到部落老家,對爸爸媽媽說,你們的兒子明天會回來,以後要注意一點。」當我們移動到昏暗的客廳時,前輩的小妹追溯她的記憶,「那時候我正好也在家,不知道為什麼警察要特別來說這件事,原來哥哥當時是政治犯啊!」簡短的幾句話,解開了家屬數十年來心底的疑惑,這似乎也才能解釋,為什麼哥哥一直要四處搬家,就害怕警察臨檢和查戶口。
「直到現在還是如此嗎?你們不知道2019年已經有撤銷罪名的公告?沒收到通知?」前輩的妻子和小妹對看了一眼,搖了搖頭,表示並不知道相關的資訊,而這一家人對於警察的恐懼始終存在,這也就是為什麼前輩將戶口登記在小妹的住家地址,自己卻帶著全家不斷地四處移動,有時甚至窩居在沒有門牌的工寮裡,以逃避警察的查訪和臨檢,因為逃避監控,遺漏了撤銷公告的公文通知,更因為巨大的恐懼,前輩將全家置於五十年前的陰影之中。
踏上歸途
時間以它獨有的方式,一分一秒的走著,在相同的節奏裡,我一邊搜尋著前輩的相關檔案,找到了他當時的獄友,一邊整理著第一次見面的影像畫面,忙得昏天暗地。
而對前輩一家來說,時間似乎特別緩慢而難熬,不過短短幾天,前輩頻繁的進出急診室,直到家屬感覺到所剩日子不多時,撥來了緊急電話通知,我立刻就跳上了計程車,飛快趕往醫院,唯恐在時間的某次移動中,就錯過了前輩的餘生。
病床上的前輩只剩下薄薄的一層皮膚包裹著骨頭,瘦弱的讓人不忍卒睹,戴著輔助呼吸的氧氣罩,他幾次想要伸出手撥掉,卻是無力的只能動動手指頭,連抬起都顯得困難;已經有些混濁的眼神四處飄移著,似乎在找尋著什麼人或有話想說,他的妻子上前靠近輕輕地詢問著,卻是意外的聽到了「身分證」三個字,當妻子將身分證交到他手中時,只見瘦骨嶙峋的雙手抖顫的將那一張卡片翻來覆去,竟是為了確認上面是否存有「政治犯」的註記。
我在那一刻突然就意識到他對於自己身上的污名,即使在彌留狀態中都無法放下,透過多方管道的協助下,當時還存在的「促進轉型正義委員會」的王增勇委員,於當日下午急匆匆將前輩沒有及時接到的罪名撤銷公文送達病床前,緩慢而細緻的將公文內容向黃家一家人解釋,而幾乎已經無法言語的前輩,艱難的吐出一句「罪名已經撤銷了?」然後點點頭沒再說什麼。當眾人都散盡後,家屬傳來了一段三十秒的影片,畫面中的前輩哼著阿美族的古調,雙手甚至還能跟上節奏的拍著,臉上有著釋然的神情,但不知道為何,我們所有人都感覺到那約是前輩迴光返照的時刻。

陡峭的三月寒風緩緩退場,和煦的陽光照耀在花東公路上,十天後,我陪伴著家屬護送前輩的骨灰返回電光部落,車就停在部落老家上鎖的大門前,家屬幾番和守顧老家的大妹聯繫,卻是得到無法諒解的回覆,怎麼也不肯前來開門讓前輩的骨灰入門向祖先辭行,「罪犯」一詞如橫亙在門上的那一道大鎖,直到前輩離世都無法被釋放。
無奈下, 家屬只能以極緩的車速,載著前輩的骨灰繞行部落一圈,途中經過部落入口意象的竹砲台、他曾經就讀的電光國小、豐年祭舉行的sefi(部落活動中心)、因為冤獄一輩子只參加過一次的Kapot(年齡階級組織),最後再駛過不得其門而入的老家,家屬噙著滿腔的傷心和遺憾,最後前往安置骨灰的靈骨塔。前輩的兒子凝視著父親的照片緩緩說道:「至少你是帶著撤銷罪名的公文走的,到祖靈面前你可以證明自己是無罪的,放心的走吧!」家屬踏著滿地的落葉離去,只剩佛經餘音繚繞在悲傷的空氣中。

延伸閱讀
政治受難者口述歷史|黃勳東|完整版
※本文摘選自國家人權博物館半年刊《向光》第8期〈押房裡的勇者:東部地區政治犯監獄與政治受難者生命故事〉
加入 琅琅悅讀 Google News 按下追蹤,精選好文不漏接!逛書店
延伸閱讀
猜你喜歡
贊助廣告
商品推薦
udn討論區
- 張貼文章或下標籤,不得有違法或侵害他人權益之言論,違者應自負法律責任。
- 對於明知不實或過度情緒謾罵之言論,經網友檢舉或本網站發現,聯合新聞網有權逕予刪除文章、停權或解除會員資格。不同意上述規範者,請勿張貼文章。
- 對於無意義、與本文無關、明知不實、謾罵之標籤,聯合新聞網有權逕予刪除標籤、停權或解除會員資格。不同意上述規範者,請勿下標籤。
- 凡「暱稱」涉及謾罵、髒話穢言、侵害他人權利,聯合新聞網有權逕予刪除發言文章、停權或解除會員資格。不同意上述規範者,請勿張貼文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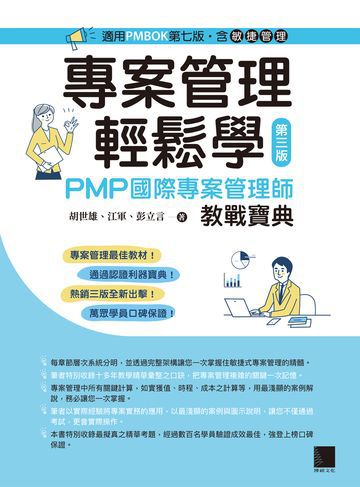




FB留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