鍾喬/時間在裂縫間穿梭

時間,總是突如其來,便訴說著似乎日常又不顯尋常的告白。讓我們從相關於詩的朗誦開始。那天,時間終於到來。我要在「台北詩歌節」的終場朗讀詩作。先是午後,掠過恆春半島的颱風,從東海岸來襲,一次不足,回返又是一襲,在中央山脈山林中茂密樹神的庇佑下,北台灣又避過一劫。
風雨欲來不來,最後仍然未抵臨,中山堂深褐色折光的木窗,在多片格子般整然有序的玻璃間,天空顯得陰沉,無雨間,突而漸次飄起細雨。我在一個休息的空檔,穿越整齊排好的大廳椅座,在廊道間回首,片刻間,眼前的寧靜與深遠,在廳堂間徘徊著一種空間中完全靜止下來的時間。
我心裡突而便興起衝動:要在遺忘之前,盡想像的全部可能,瞬間冒出幾些詩行來。我打開電腦頁面,在寬敞的休息室臨門長桌上,寫下「無題」兩字。我心想,這是當下對待詩行字句的最好標題。我的詩行,想去回應那在時間中靜止的空間。腦海中的畫面,是廳堂裡迴廊間延伸的兩道大理石樓梯,我寫著:
沿著廊道的梯間
時間 似乎在瞬間
完全停止下來
等待 頌詩與提琴
朝向未知的 遠方
我於是在登台朗誦時,就這麼毫無預警地脫口朗讀這幾行詩。我也不知道為何會是:遠方且未知。但,我直覺地認為是拾階而上的梯間,給予我這樣的想像。因為,詩,被寫下來,便成為文字的記憶;一旦被朗讀,則像似莊子在〈齊物論〉中所言:「吾喪我」。亦即,當下的「我」已埋葬前一刻的「我」。這也是劇場常言的「當下」。
歷史建築始終有一種記憶的魅力,並非空間可以界定的。當夜色降臨,白日裡由天窗透進來的光,盡數退逝而去,聲音與光源獲致天賜的能量,在時間的穿梭中,堆疊著寓言、畫面、光影、安靜地等候及其他……都被收攏在誦詩聲中。來自法國的女詩人「Aurelia」,歐黑利亞是雙語詩人,以法語及南法曾慘遭打壓的奧客語作為創作的語彙。
她朗讀時,整個由時間濃縮起來的大廳,迴廊間彷彿穿越伊的雙重身影:既是光照下側面的法語,也是影子側面的奧客語,兩者都是生命的側面,融為一體時,成就了她在誦詩時,以荷馬史詩《奧德賽》為題,借用了當下的一體兩面:一則以法語敘事,一則以奧客語抒情吟唱。像似浪潮下駛向洋面波濤的詩行,時而傳出夜暗女詩人在岸上的低吟。那被禁閉的奧客語,發出吟唱時,有種禁閉中的抵抗之美,我這麼感受著,於是我說:「這世上被遺忘的事物。通常是最具生命力的事物。」奧客語如是,台灣客語曾經在戒嚴時期,不也如是。
提琴聲總像也在提醒著:這世上被遺忘的事,如果從大廳裡日本敗戰受降儀式傳來,光復的也已經是被遺忘的前情記事了。當我誦詩,我說:「我對大提琴與詩結合的著迷,始於多年以前,在廢墟華山的大煙囪下搭帳篷演出時,我扮演詩人腳色,那位來自日本橫濱海邊的魔幻提琴師,隕石般以他的琴聲擊倒我的詩行……那是每一個剎那的每一顆隕石,從夜空而降。」
誦詩後,我為了一場稱作「斷面裡的劇場」展示,來到一處防空洞裡,展示的物件在光影間呈現,寶藏巖的斷面記憶,在身體與靈魂交錯地域徘徊。一個據說是多年以前,在斷面帳篷劇中的腳色──死去士兵的靈魂以「舞踏」之身,現身在光與影的錯落間。舞踏,燃燒的身體如何轉作戰爭的想像?來不及思考之際,便發現一位劇本中的人物,沉思地走來。他,就是詩人,無誤。
詩人坐下,在靈魂的身旁。兩人有一段低沉的對話:「告訴我,你的下一趟旅程往哪裡去?」靈魂問。詩人沉默半晌,抬起頭來,似乎很不是專注地回話,說著:「我昨夜遇上杜甫了。」這接下來的一應一答,應該都充滿不洩天機的戲劇性吧!我想。靈魂立刻搶時間快答:「哈哈!這玩笑開大了!」倒是詩人回應得很從容,他說:「我們是劇中人,情境是劇作家設定的,沒什麼是不可能的……」
於是,想像的時空瞬間取代了現實的時空。詩人說他和「安史之亂」時期的杜甫,相遇在兵荒馬亂的道途上。據他轉述,杜甫說:來到「石壕村」,寫下〈石壕吏〉這首紀錄片一般的知名詩作,開頭就這麼說:
暮投石壕村,有吏夜捉人。老翁逾墻走,老婦出門看。
說的是:杜甫在兵燹之亂中投宿到「石壕村」的一戶平民百姓家,半夜敲門聲緊促,是來抓伕的,於是老翁翻牆逃避,獨留老婦前去應門。接下來的詩行寫著:
一男附書至,二男新戰死。存者且偷生,死者長已矣。
室中更無人,惟有乳下孫。有孫母未去,出入無完裙。
也就是,老婦向抓伕的軍吏說道,伊收了么兒來信,說是兩個哥哥都已戰死沙場。現在,室中已經無人可去從軍,出入連完好的衣服都沒得穿。
最後,杜甫說他在夜深人靜的孤寂中,像似聽見有人啜泣之聲。清晨道別時,就只剩老翁留家中,因為老婦被抓去充軍了。揪心的詩行如下:
夜久語聲絕,如聞泣幽咽。天明登前途,獨與老翁別。
剛轉述完杜甫趁著破曉奔,再次登上流離之途,忙不迭地,詩人急著轉換另一魔幻的場景。情境一轉,他向士兵的靈魂說了一段,他自己在劇本裡發生的故事。他說,他也遇見一家人,父親被徵兵抓伕去,母親苦苦等不到父親回來,卻不期然收到一封父親從炮坑捎通訊兵帶回來的家書。他形容,女兒摀臉,而後悲泣;母親慌忙取信過來,看信。拿給在暗處的兒子,兒子讀信,一旁出現父親的背影。空氣中,傳來父親的聲音,是由詩人以低沉的口吻,代父親朗讀信件的聲音:
「戰爭是殘酷的,這誰都知道;有誰能料想到,竟然須去面對我方砲彈的轟炸,或許會因此喪命。但,我不想在地牢……等死神的召喚……我想了不是很長時間,因為我不會有其他選擇。若我沒被自己的砲彈擊中,就能換一條命回家……我想回家,因我被視作叛亂犯羈押在地牢裡……」
兒子:父親,他是被強迫上戰線的……
母親:他想回來,換一條命回來,和我們在一起……
兒子:不!他被強迫的……
兒子將信交還母親,她拿起信,口中喃喃念著信中的最後一段,將信交還給女兒。
這時,轉身離開的詩人,回頭望見場上正在排練一個場景:靈魂恰似老兵般,在時間的角落,啜飲著一杯斟得滿滿的高粱。母親與女兒在戰火中,邀請攝影師來拍一張合照,在母親充滿悲傷的眼神裡,女兒刻意調皮地裝鬼臉,一心溢出相框外,突兒一陣風吹來,女兒的裙襬飛了起來,身體也隨風飛了起來,母親跟上,也飛了起來,但那場景幾乎是一段離散之舞,在斷面的裂縫間浮沉。
詩人想去和靈魂說些什麼。未料靈魂竟若死去士兵般橫躺地面,母親說著一則伊父親二戰時在婆羅洲埋戰死同袍的往事。「冰冷的屍體,一具具被扔進坑裡,倒上汽油,焚火燃燒……這時屍體遇熱會突然坐立起來……父親說。」
伊說著,在劇中說著,自己父親真實的記憶。靈魂突然間坐起身來,望著手裡握有一本布萊希特詩集的詩人。劇本中的女兒是一個啞巴,她在未來或過去的一場戰事中,抬起頭,恰好一顆炸彈,在她上學的路上轟然。她目睹,老人的頭顱裂開,一個嬰兒的眼珠在廢墟裡滾動。於是,她眼睜睜而失語,對世界,對老師,對同學,對父母。失語。
但,在這劇情發展到最為緊繃的時刻裡,她瞬間搶來詩人夾在腋下的詩集。映著裂縫滲透進來的微光,用盡身體殘存的氣力,喑啞地朗讀著四行詩:
在牆上用粉筆寫著
他們要戰爭。
寫這句話的人
已經死亡。
詩人接著說著:布萊希特,1937,歐戰前夕,有士兵在牆上用粉筆寫著。

加入 琅琅悅讀 Google News 按下追蹤,精選好文不漏接!
逛書店
猜你喜歡
贊助廣告
商品推薦
udn討論區
- 張貼文章或下標籤,不得有違法或侵害他人權益之言論,違者應自負法律責任。
- 對於明知不實或過度情緒謾罵之言論,經網友檢舉或本網站發現,聯合新聞網有權逕予刪除文章、停權或解除會員資格。不同意上述規範者,請勿張貼文章。
- 對於無意義、與本文無關、明知不實、謾罵之標籤,聯合新聞網有權逕予刪除標籤、停權或解除會員資格。不同意上述規範者,請勿下標籤。
- 凡「暱稱」涉及謾罵、髒話穢言、侵害他人權利,聯合新聞網有權逕予刪除發言文章、停權或解除會員資格。不同意上述規範者,請勿張貼文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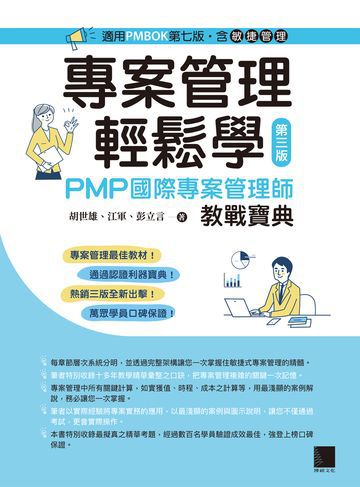




FB留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