蔣亞妮/停止吧,時間——當桑塔格遇見杉本博司

客席主編導讀
朱嘉漢(小說家)
文學能繼續存在的理由,在於書寫本身,透過懷疑的一再確認。散文的直率、透明性,有時我們會誤以為那該是完整的、真實的。蔣亞妮是散文寫作者,也是懷疑者。透過對攝影師杉本博司的觀看,對影於蘇珊‧桑塔格的《論攝影》,吞吐於自身的寫作質問(如「散文不能說謊,也是一個謊言」這樣的悖論。)。然而,答案就在這多重互文的質疑中,暫且確認,反思所見的片刻,那喊停的瞬間,正是我們窮其一生迫近的,所能見的最真實美好的片段風景。
攝影就是
凝結時間的裝置
我總是在影像裡重新理解與學習書寫散文這件事。
那是鍛造之術,而《鋼之鍊金術師》告訴過我們,情感等同物件,並不能從無中生出,最多只能從既有中幻化成世間一切有名無名事物。因此,攝影家都是真正的散文大師,反向的通道也一樣成立。羅蘭‧巴特(Roland Barthes)教會我辯認「此曾在」,以及贈予世界一帖觀賞攝影時的情緒解藥,告訴我們「知面與刺點雖彼此對立,但又可並存共現於同一照片中。知面是一種廣度量的延伸,刺點則是干擾、穿透它的瞬間強烈一擊。」更如他所說:「不管照片中的主體是否已死去,所有的攝影都是此一死劫終局。」將那一瞬間反射於現在,不就是文學的入門解讀法,今天如此、昔日這般,以此習得了「對照」。
在散文與攝影中流動,我最動情的地方,總是它們與時間的關係。森山大道(Moriyama Daido)說過的:「攝影就是凝結時間的裝置,所有照片都是決定性的瞬間……人類總是抱持著停止時間的慾望,而相機剛好可以滿足我們。我每天都想凝結眼前的事物,完全無法克制這個慾望。」或者他的另一段名言,與其說攝影是記錄,毋寧說攝影是記憶,於是經過一連串記憶積累的歷史過程,攝影成為一種時間的化石,更是「光影的神話」。種種「攝影」二字,非常適宜切換成「散文」,為什麼不是長時間以來,人們總說被攝影取代的「繪畫」呢?蘇珊‧桑塔格(Susan Sontag)的名著《論攝影》幾乎是滿紙珠璣,桑塔格的正確讀法是先學著放棄畫下重點,才能讀進整體。她很好地解答了我在觀賞畫與影間的拉扯,如此寫下:「攝影把繪畫從忠實表現的苦差中解放出來,讓繪畫可以追求更高的目標:抽象。」

神之一瞬
繪畫沒有留戀的去往抽象之地,留下真實的責任給攝影與散文,「實」是個有趣的字,真實、忠實、誠實與寫實相互靠近,卻不等於彼此,比如「真實」,它崇高不已,卻從來都不是一種直接霸道的寫實,誠實也是經過篩選的忠實;這在各自的領域裡,都引起過不小的論戰,不真、不實、作假、擬態……種種指控,然而桑塔格早已藉此答彼,照片(散文也是如此)從來「不是真正地存在什麼,而是我真正地察覺到什麼」,在兩者的創作上,沒有一個投入的創作者是「無意識」的,即使只是蟬聲或雨點、死別到愛恨,都是觀察到的現象、都是微物之神的欽點。因此眼見為實,卻不一定是真。
當然一張照片與一篇散文仍有不同,比如照片從來不描寫,描寫的是背後被消音的語言,可以把一本散文想像成一部攝影集,卻很難把一張相片,完整地擴寫成一篇散文。語言描寫,是時間中的一種活動,第一次讀桑塔格《論攝影》時,被困在一段描述裡出不來,她寫下自己在1945年7月的聖莫妮卡一家書店裡,偶然看到了「貝根貝爾森集中營」和「達豪集中營」的照片。「我所見過的任何事物,無論是在照片中或在真實生活中,都沒有如此銳利、深刻,即時地切割我。確實,我的生命似乎可以分成兩半,一半是看到這些照片之前(我當時12歲),一半是之後,儘管要再過幾年我才充分的明白他們到底是什麼。」與桑塔格存有的巨大時差,讓我更緩慢的隔上幾年才理解這是什麼「神之一瞬」,在許多攝影展覽之間流浪,不管是提供故事或者選擇靜默的,許多時間裡面——它們始終只是照片。直到遇見杉本博司(Hiroshi Sugimoto)的海,它們當然不是歷史中的單一事件或者苦難,卻依然讓我如同桑塔格般感覺到「有什麼破裂了,去到某種限度了」。

杉本博司《海景》系列
寫完第三本書時,在拍賣上巧遇了杉本博司《海景》系列的全新美版,狠心買下。那些藍綠黑灰斑斕的海,是杉本博司自1980年代開始的攝影計畫,我拿到的版本裡,海被停止在2017年。從日本海到澳大利亞與紐西蘭之間的塔斯曼海域,有什麼東西分割了我從此的書寫脈絡,是無法被擴寫的海洋歷史,更是我一生中漫漫無來由的悲傷。種種家與人的傷害並不是悲傷的來處,我知道它必來自某種古老虛無的地方,如同集體潛意識般地植在體內,直到閃電劈向海洋、直到藍色在無窮遠處變成透明、直到變成青苔……我才理解那來處,無比擬似大海。
杉本博司拍攝《海景》(Seascapes)系列時,所有的海景照,其實都是站在陸地,往海拍攝的,他說那些風強、浪碎、雲多的日子裡,都是無法拍攝的(好像也是不能寫作的日子)。而最適合拍攝海景的地點,往往是高於海面100公尺處的陡峭斷崖,「越適合拍攝的地點,越是遠離人煙」,越深鑿的書寫,也越是沒有人跡。沒有人,並不只是物理上,更是心靈的所在,若鐵了心要寫、要拍攝,人潮中心市聲滾沸,也無法阻擋,任千萬人來往,心中都是沒有的。
並不是沒拍下,
而是拍太過了
我們一生所寫出的所有故事都是過程,攝影是、散文也是,杉本另一個知名的攝影系列《劇場》,是經由播放一部電影的長曝光時間,完成一張照片,在他的散文集《直到長出青苔》裡,也回應了對此創作的提問:「並不是沒拍下,而是拍太過了。」他確實拍了一天,卻是一片白影,白影更是時間,就像杉本博司大多數的作品,也都是時間。比如他在散文裡提到,某段時期他與妻子在紐約開設骨董店,這使得他能很好地識別文物與時代,他曾以一個鎌倉時代裝裱舍利子的容器,裝禎自己的「海景」。這樣一來,若有人問起這作品的年代,便有許多可能,可以是現代到鎌倉、現代到太古的海,更明確地說,一如他許多作品的製作年代,年代都是「時間之箭」,「時間之箭從開天闢地開始,通過鎌倉時代,來到你的眼前。」
閱讀《直到長出青苔》,是一場非常後設也非常冒犯的過程,杉本博司終於走出作品,以他的語言書寫動機、書寫時間,自白般地說起,自他使用名為「攝影」的裝置以來,一直想去呈現的東西,就是人類遠古的記憶。「那既是個人的記憶,一個文明的記憶,也是人類全體的記憶。」攝影師說明作品、創作緣起,即便如我一般曾迷離在海景與劇場的觀者,都會產生落差,落差更大時,便成偏差。其實不只是攝影,所有的創作者都如此,許多的分享發表會、新書座談、展後映後講座,都像是把舞台暴力的鋪展到創作者腳下,你得自己說明自己,明明已經完成了繪畫、樂曲、書籍與攝影,卻得再用話語重新填充;常常忽略了創作本身就是寂寞,它的形成過程並無法被破解與翻譯,月亮如何牽引潮汐,總有在引力之外的神祕學,如果萬物都可以被解釋,就不需要去創作。桑塔格的先見,永遠會成為一種我書寫時才參透的後見之明,她說:「繪畫或散文描述只能是一種嚴格地選擇的解釋,照片則可被當作是一種嚴格地選擇的透明性。」於是明白,當所有的事物都淪落解釋,它們全都失去了透明性。
或許這也是我翻開《海景》的次數,遠遠多過《直到長出青苔》的原因。但若是試圖拆解杉本的散文,將文的布帛割裂,為我拼用,許多片段都像是最好的創作論。「911」之前,杉本曾經拍過世貿雙塔,當他拍攝這座現代主義建築,以沒有裝飾為裝飾、以不宜居住為宜於居住的存在,他選擇使用了大型相機,但拍攝出來的影像卻是全然模糊,「因為我將相機焦點設計在比無限大還要遠的地方,透過相機的設定,勉強使影像模糊。這樣說吧,我想要窺視這世界不應存在、比無限還要遙遠好幾倍的場所,卻被模糊給吞噬了。」後來,現代摩天樓真的變作了紀念碑,不知道是模糊吞噬了時間,還是時間的原貌本就模糊不清。就像杉本獨愛的日本傳統「能劇」,他認為「能」是時間的樣式、「能」是時間的流動化,我們所在的現實裡,時間單向地從過去延伸至未來,「能」裡頭,時間卻是自由來去的,夢是它乘坐的工具。

散文與攝影
經常共享的真實?
因此,散文與攝影經常共享的真實、被要求的真實,本來就是一場騙局。杉本在書裡有許多段設計好的假問答,提問與答者都是自己:「日文稱照片為寫真,不就是寫下真實的意思?」「說照片不會說謊,就是一個謊言。」在不存在的提問裡談論真實,是一種惡趣味,卻也接近一種正解。這世界上不存在不說謊的藝術創作,即使是在時間裡頭,都得乘著夢跳島、穿越,卻沒有人指責時間說謊,因為你知道它絕對有其不真實。在某一種極端的散文寫作裡,也會讓我想到另一個攝影大師黛安‧阿巴斯(Diane Arbus),曾如此界定攝影,「是一種下流的玩意兒——這也是我喜愛攝影的原因之一,我第一次做攝影時,感到非常變態。」那種快感,很接近桑塔格破譯的:「相機不能強姦,甚至不能擁有,儘管他可以假設、侵擾、闖入、歪曲、利用,以及最廣泛的隱喻意義上的暗殺。」散文也可以還擊、破壞與公然說謊,那種暴力幾乎像是一場情色成人秀,撐著真實大傘,公然做愛與殺害。說是為了還原,卻只還原了自己的慾望與痛,散文不能說謊,也是一個謊言。
我屢次穿梭在杉本博司洗出的淡色世界裡,就像聽桑塔格在耳邊說話,比杉本博司早上十五年誕生與活躍的桑塔格,不知會如何論及這位被當代稱為「最後一個現代主義者」的攝影作品?桑塔格倒是說了很多關於班雅明(Walter Benjamin)的事。
當中最有趣的,應該是提出班雅明嗜好引語(尤其是格格不入的引語)的習慣,在她看來幾乎是一種「超現實主義」的嗜好。漢娜‧鄂蘭(Hannah Arendt)如此記憶過班雅明這個小喜好:「他三◯年代最大的特點,莫過於他永遠隨身攜帶的那些黑封面的小筆記本,他孜孜不倦地以引語的形式,把每天生活和閱讀中所得,像珍珠和珊瑚般記錄下來。有時候他會挑一些來大聲誦讀,像稀罕而珍貴的收藏品那樣出示給人看。」因此《論攝影》的最後一輯〈引語選粹〉(A Brief Anthology of Quotations(Homage to W.B.)),便翻玩了這個很班雅明的喜好,錄下許多桑塔格特意蒐集而來的引語。
因為無法擁有,
因此用攝影偷取它
當歷史的進程使得各種傳統元氣大傷,班雅明一直在試圖搬運珍貴的碎片,廢墟的重建者非他莫屬。這當然也是時差後頭,我才明白的道理,從前的我對於搬運碎片、使用引語,有著生理性的排斥。直到海切割了傷口,時間開始成為亂碼,我才明白不管是哪一個人名,都是因為爬上前人肩頭能更好的眺望、都是為了說出後頭自己的話。因此,我竟也開始建立了新的檔案資料夾,開始了自己的蒐集。這讓我想到杉本博司曾經有機會入內拍攝京都「三十三間堂」的國寶「千體佛」,他在有限時間內的每一個早晨裡,無比慎重地按下許多快門,他說:「因為無法擁有,因此用攝影偷取它。」這成了我收藏的一段引語,為什麼癡迷書寫散文?因為這世界還有許多我想偷取的事物。
有趣的一件小事,其實杉本博司也真正遇見過桑塔格。在另一本《現象》中,有篇〈臨刑者小曲〉,他寫下自己曾經承接了蘇珊.桑塔格未盡的選影工作,於是他反覆看她留下的資料、聆聽她講座的錄音,甚至為了她所提到的一句電影台詞,找來DVD反覆觀賞。
生死的接力、人名的穿越,全是時間的簡史。在攝影照片裡、在幾千字的文字裡,時間被停止了片刻,然後,時間再被啟動與串接了片刻。我們需要的,從來只是片刻。
加入 琅琅悅讀 Google News 按下追蹤,精選好文不漏接!逛書店
猜你喜歡
贊助廣告
商品推薦
udn討論區
- 張貼文章或下標籤,不得有違法或侵害他人權益之言論,違者應自負法律責任。
- 對於明知不實或過度情緒謾罵之言論,經網友檢舉或本網站發現,聯合新聞網有權逕予刪除文章、停權或解除會員資格。不同意上述規範者,請勿張貼文章。
- 對於無意義、與本文無關、明知不實、謾罵之標籤,聯合新聞網有權逕予刪除標籤、停權或解除會員資格。不同意上述規範者,請勿下標籤。
- 凡「暱稱」涉及謾罵、髒話穢言、侵害他人權利,聯合新聞網有權逕予刪除發言文章、停權或解除會員資格。不同意上述規範者,請勿張貼文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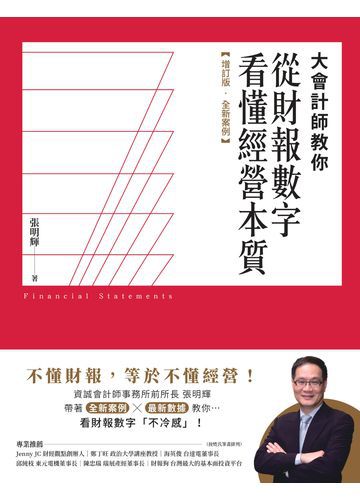






FB留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