黃春明vs.羅智成/詩與小說的二重奏(下)


對談時間:2022年8月3日下午二時至五時
對談地點:明星咖啡館
陳昱文╱記錄整理 圖/本報資料照片
●黃春明:在兒童內心的世界裡,什麼都有可能發生,比如我有一首詩叫〈我有恐龍多好〉,是這樣寫的:「我有恐龍多好/我騎恐龍上學校/路上的行人汽車都跑掉/到了學校/訓導主任叫都不敢叫/校長遠遠看到我揮手笑一笑/看,我有恐龍多好//我有恐龍多好/我騎恐龍上學校/路上的同學/要搭我的恐龍一起上學校/哼!那我要看看/那一位同學對我最好/看,我有恐龍多好」,有童心的讀者看到這首詩,應該會會心一笑,但也有一位小學校長,讀到之後卻說:「怎麼可能會騎恐龍上學?也不尊師重道!」其實對小孩豐富的想像力來說,什麼都有可能發生。我這首詩的靈感來自生活中的真實經驗,有些小孩喜歡在家的牆壁上亂塗鴉,我二個孩子也是,所以,我和孩子約定,我們可以在一面牆壁上玩畫畫,別的牆壁都不能亂畫,孩子畫下面,我就畫上面。有一天,小兒子畫了一隻恐龍,一個梯子,一個小孩爬上梯子,拿著一支棒棒糖要給恐龍吃。因他還不會寫字,我太太提筆幫他寫上他的意思「恐龍恐龍不要哭,棒棒糖給你吃!」。我就是從這個畫面寫成這首詩。
有童心的人,會平等看待小孩,跟小孩產生共鳴。我很喜歡小孩,只要有小孩子到我們家來,大人聊天時,我就會跟小朋友玩,為他們說故事。我會跟他們說,我今天是黃同學,你們就是老師,要幫我打分數。結果分數從一百、兩百、三百,跑到無限大。我家還有很多小鞋子,去美國時忍不住就買了好多小皮鞋,我很喜歡小孩!
●羅智成:我覺得騎恐龍上學就像騎重機車一樣,超酷的!這首詩會讓我想起迅猛龍,迅猛龍的形象就很像一輛摩托車。為什麼小朋友會對恐龍特別著迷?包括小時候的我,和小時候的大兒子和老三,都有很長的時間耽溺於和恐龍有關的事物?可能是因為牠有遠大於現實陸地動物的尺寸,同時已不存在於此刻的世界,所以讓充滿想像力的人有了杜撰、遐想的空間。在《侏儸紀公園》還沒上映的一九八二年,我出版了《傾斜之書》,最前面有一首詩就叫作〈恐龍〉,當中我把恐龍化石比喻為一艘船:「空虛的頭顱/鬆脫了森嚴、綠色的歷史/弧度優美的頸項,/是修長的狹橋/連接飛鳥的視野/和龐大,憂愁/必然腐朽的軀體/成排的肋骨/徒然的槳/在平滑如水的地面/船首蹺起/顯然是重重地/撞在礁石上」。
明星咖啡館是最早的
台北文學館
●羅智成:最近台北市文化局與文化界正共同推動台北文學館的籌設。其實最早的台北文學館說不定就是明星咖啡館呢!當年有不少詩人、作家都是在此寫稿、聚會。我還記得高中時代第一次看到你,就是在明星咖啡館。現當代文學是台北的驕傲,也是重要的文化資產,特別是上個世紀六◯年代起,傑出作家多如繁星,文學社團和出版品也蓬勃發展,我個人就深深受到影響。
如果說廣義的台北文學館,我覺得以前整個重慶南路的書街及周遭地區可以當之無愧。在我很小的時候,母親在開封街的公共工程局上班,我被帶到辦公室後常常就一個人在附近的街道閒逛,尤其是轉角後的重慶南路。重慶南路那時候可熱鬧了!書店一家接著一家,各式各樣的都有。不過一般的格局是:最前面擺字典、六法全書等工具書,最上面擺《戰爭與和平》、《約翰克里斯朵夫》等大部頭名著,中間部分是以文庫為主的文學書籍,後半段則有日記本、信封信紙和各種參考書,書店的另一半通常是玻璃櫥櫃,裡面擺著比較昂貴的文具。中學後,我常去「商務印書館」買一本十元起跳的「人人文庫」,在此有最周延或相對冷門的各國文學、哲學經典,都是小如手掌的40開本。那時才知道「明星咖啡館」就在「排骨大王」隔壁,而周夢蝶則在熙來攘往的騎樓下擺攤、打坐、寫瘦金體書法。從此就常常跑到樓上的咖啡館,聊天、寫稿、目擊著名作家們的聚會。一直到現在,我還清楚記得許多好吃的小店都在重慶南路的巷弄裡,牛肉麵、江浙小點、武藏日本料理、公園號的酸梅湯、中山堂旁的36種口味冰淇淋等等。我的第一本詩集《畫冊》就在「明星」對面巷子內的打字行完稿的,再自費出版,不久竟然就出現在周夢蝶的書攤上了。
隨著書街往外擴充一圈,就是西門町了!我會背著書包,去探索另幾家知名的咖啡廳,還有羊令野、羅門、張默等詩人常去的國軍文藝活動中心,瘂弦、段彩華、阮義忠在樓上工作的幼獅書店,龍族詩社聚會的天琴廳,或去中華商場買古典音樂和搖滾民謠唱片。現在想想,那些地方都是台灣的現代文學發生的現場。

●黃春明:明星咖啡館附近的牛肉湯麵、苦瓜冰淇淋、窄巷裡賣衣服、碗盤的店家,我也很熟悉呢。明星咖啡館當然最熟了!它好像是我的寫字間。以前要租一間房子專心寫字創作,可是很貴的。明星咖啡館就太方便了!舒適、自在,熟了以後,他們還會幫我代接電話,真是賓至如歸。簡錦錐老闆對我很好,我可以擺一個杯子在這裡一直寫作,他特別交代服務生不要收走杯子,讓我有個專心創作的空間。顧客變多以後,便改在咖啡館三樓寫作。明星曾經歇業一陣子,那時簡老闆還特地將明星的圓形咖啡桌、椅和幾套咖啡杯組送給我,現在我已將這些物品,移放到宜蘭大學圖書館裡面的「黃春明體驗行動館」。
明星咖啡館生意很好時,在中山北路也開了一間店,比較安靜,我也常去那邊寫作。有一天,我發現一位白俄羅斯老人在廁所裡暈倒,我無法把他拉出來,趕緊請人協助,救了他一命。那位老人就是當初合夥開明星咖啡館的艾斯尼。大家都知道明星跟俄國人的淵源很深,俄國大革命之後,許多俄羅斯貴族或軍官大量逃難到上海,再輾轉來到台北。這群白俄人原本在上海教鋼琴、芭蕾,也有來台灣後從事手工胸罩的製作。
在台北的俄羅斯人有一個二十多人的小交響樂團,有一次蔣方良幫他們到中山堂正式演奏柴可夫斯基,中正廳前排的聽眾除了俄羅斯人外,也保留座位給一些黨國要員,這些達官貴人沒有空來就把票送給為自己管家、燒飯的僕使,結果演奏開始後,盛裝出席的俄羅斯人漸漸聽得淚流滿面,而熱情洋溢的僕人們則喧譁地此起彼落打招呼,場面頗不協調。我當時也在場,看到白俄羅斯人掉眼淚非常感動,印象十分深刻。台灣人普遍對古典音樂開竅較晚,認識也都不深,當時的羅東只有木材商家裡有錢才能聽古典樂,他們教了我,我才開始認識並喜歡古典音樂,理解到那優美的旋律如同詩一樣,蘊含深刻的美感。現在我們家還收藏很多古典音樂CD。
成為有抵抗力的
「壞孩子」
●黃春明:讀書、寫作、聽音樂,看起來是一個斯斯文文的好學生才會做的事情。但是很矛盾的,我從來就不是一個好學生。在那個年代,要做一位好學生,就會有許許多多的約束、很制式化。過去我們有太多壓抑和太多口號了,要背這個、要背那個,像「青年守則」十二條,還有一些八股寫作的框框,形式化得太厲害了!那樣的教育方式和我的個性與認知差別很大,到現在我還是堅持我的想法,認為教育應該採用「地震式」的教育,也就是常讓年輕的孩子釋放情緒,宣洩活力,容忍他犯點小錯;就像頻繁的小地震一樣,隨時把能量釋出。假如沒有釋放情緒的機制,一直用高壓的態度來進行管理,壓抑就會累積成一座火山,就會有三十年一次的大地震。我認為可以讓小孩先當個壞孩子再來學好,學好的壞孩子就會有面對各種困境的抵抗力。
青年時,我的體育是十項全能,打架更是在行。有時我都意識到不能打架,拳頭卻已經揮出去了。念中學快被退學前,我還被打群架的人,在右眉角處劃了一刀。還有一次我是和軍人起衝突,被帶到警察局二樓,對方的長官知道我是羅東橄欖球隊隊長,就不跟我計較了。因為我們球隊比賽時,他們都會來看我們打球。
我常覺得命運就像打彈珠台,砰一下彈珠射出,再來就靠後天物理作用了,看看會遇到誰,發生什麼遭遇,或展開怎樣不同的故事。我運氣比較好,民國四十幾年交通並不發達的時代,一位來自宜蘭鄉下的孩子,竟還可以跑到台北、屏東念書。很可能,我早兩年或晚兩年也考不上師範學校。
雖然我的成長故事還滿精采的,但是目前沒有考慮寫自傳。很多人寫自傳都把自己寫得很神勇,或寫得太好。這跟我的性格不合。我傾向於用小說形式把我過去的經驗或想法表達出來。它看似虛構的,卻隱藏著更多的真實。我和陳映真是在《文學季刊》認識的。左派的文學觀特別關注現實社會,對社會比較有批判性。但是有時候並不需要理論的引導,只要跟著自己的良知和對公平正義的信念,你對生活周遭的各種現象自然會形成清楚的態度與想法。例如,我有對後殖民現象的批評,在台灣還沒介紹薩伊德(Edward W. Said)的《東方主義》時,我就寫了〈蘋果的滋味〉、〈莎喲娜啦‧再見〉。當時我也談從日本看第三世界的文化歸依與超越。在歷史上許多權力或角色的關係是相對的,誰也不能逃避普世價值的檢驗,雖然台灣被日本殖民過,但我們也殖民了當時被稱高砂族的原住民。我寫了一篇「戰士,乾杯!」是說屏東好茶村的故事;在一個魯凱族的家庭裡,竟然有日本兵、八路軍、國軍、原住民,都是為別人在打杖,也因種種因素和矛盾,還會自己打自己人。
●羅智成:談族群議題最能檢驗一個人的客觀性、同理心以及包容的胸懷,要讓不同文化背景、不同歷史記憶的人和諧相處,需要極大的智慧與進步的文明。你的作品顯現出的思考深度與氣度是當代一些政客與議論者難以企及的,也許也就只有當年左翼文青的世界觀裡,能約略保有某種「兼愛」的宗教情懷。
文化的多元很重要,像盛唐的文化就很多元。只要奠定了主體性,文化的血脈越多越好,才容易形成多樣、包容、健康的社會。相反的,古埃及和某些文明裡的近親通婚,就造成許多遺傳上的問題。我一直覺得在生活文化層面談淵源論很奇怪,只要對我們來說是優美、喜歡、好用的,久而久之就會成為我們的文化。我也相信,一座島嶼的開放,失去的總是比得到的少,得到的總是比失去的多。
東方式教育往往偏執於在無菌狀態下控制孩童成長方向。所以當他們長大,遇到真正的問題時,就沒有足夠的生活經驗、參考座標和成熟心智去解決。我也傾向於某種「壞孩子」的教育觀,一種半野生的,或放養式的教育體系,比較能產生我理想中「高貴的野蠻人」或「日神阿波羅與酒神戴奧尼修斯的複合體」。在過度社會化的過程裡,為了融入社會,人的思想和感受容易受到內外在的脅迫而益形僵化、制式化。這是可以理解的,人類總有潔癖,希望大家一致,不希望有人搗蛋。但我認為東方社會仍應該更鼓勵開創,也要更容許多元的性格和價值觀,更好的未來才會在此發生。
●黃春明:文學和教育都應該來自真正的生活。鼓勵我們的下一代真正的去聞、去摸、去跑、去跳,陽光與風雨、跌倒與受傷是不可替代的,它會讓我們的生命更豐富、扎實。不要老是耽溺於真真假假的媒體環境裡頭。我最近對生命有意識地去感覺,是與你對談的現在,陽光自窗戶灑進明星咖啡館,雖然這個古典雅致的空間已超過半個世紀,陽光還是那麼神采奕奕。我們倆也曾在東華大學教過書,我常去志學街用餐,在寬闊的花東縱谷徜徉,記得東華校園有兩個湖,還有野兔和環頸雉,還有好朋友李永平等等。我更常在身旁的大自然裡去意識到生命:在河邊的野薑花是最美的,而且很香。台灣百合則在我們北方澳整個山頭都是,酢醬草開著小小的粉紅色花,也很美。植物自有一番哲學道理,例如九重葛不需要你一直澆水,只要有危機感,就會趕快開花。木瓜樹如果不生果,就用刀輕輕劃一下再撒鹽巴。也聽人說將母蝦的眼睛剪掉一隻後,母蝦就開始產卵。關於水果,我覺得蓮霧有蓮霧的味道,釋迦有釋迦的味道,現在的鳳梨太甜了,台灣的飲食滋味很豐富,每種水果都要擁有自己的個性才對。
●羅智成:的確,現在台灣的水果普遍太甜了,人類為了自己的喜好,正大規模改造動植物甚至寵物的習性,原先的個性都消失了。我也很喜歡花,大理花、百合、桂花、玉蘭花……我偏好密密麻麻的小花,像滿天星。我也喜歡明豔的九重葛,雖然它不是花,是太陽的私生子。我喜歡一切野花。我曾書寫過南投竹山溪邊的野薑花,楊牧在《傾斜之書》的序中特別將這些句子引出來:「在竹山有個美麗平靜的下午/山邊種有扶手瓜,軟枝黃蟬/雷聲在雲層的地板上遊走/當天色漸暗而溪邊款款一亮/是成群成群的野薑花」。(下)
十月《文學相對論》
林達陽vs.陳雋弘將於10月3-4日登場 敬請期待!
加入 琅琅悅讀 Google News 按下追蹤,精選好文不漏接!逛書店
猜你喜歡
贊助廣告
商品推薦
udn討論區
- 張貼文章或下標籤,不得有違法或侵害他人權益之言論,違者應自負法律責任。
- 對於明知不實或過度情緒謾罵之言論,經網友檢舉或本網站發現,聯合新聞網有權逕予刪除文章、停權或解除會員資格。不同意上述規範者,請勿張貼文章。
- 對於無意義、與本文無關、明知不實、謾罵之標籤,聯合新聞網有權逕予刪除標籤、停權或解除會員資格。不同意上述規範者,請勿下標籤。
- 凡「暱稱」涉及謾罵、髒話穢言、侵害他人權利,聯合新聞網有權逕予刪除發言文章、停權或解除會員資格。不同意上述規範者,請勿張貼文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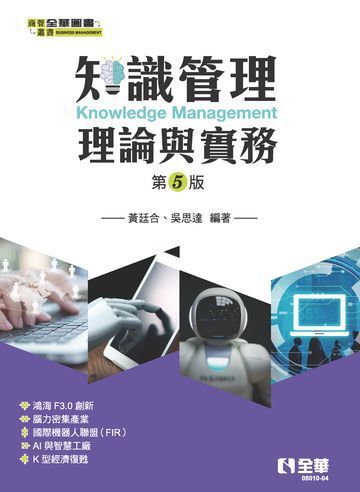







FB留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