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銘亮/帝王家的鏡子

他夢見自己醒在花園之中,抬起頭揉揉臉,桌上的琉璃紙鎮壓住一張條幅,卻只寫著幾個雞蛋大的字:「我對面的兩個我」,對峙那餘下的不成比例的大面的空白。這幾個字也不知道是不是自己寫的,夢中人不會想到核對筆跡或者任何服膺現實邏輯的事。他站起來,藍天微雲之下一絲兒風也沒有,湖面的波紋如大理石浮雕,梅花桂花盛開卻不香,這才發現山石花樹、水榭亭台原來都是畫,透視的幻覺。第六感告訴他如果這裡不是花園,就該是帝王的書齋。左手邊有一面鏡子,他一照,照不出自己的臉來,慌了;右手邊卻是一扇與鏡子造型相同的門,他不敢走出去。正對他的是一座藻梲的戲台,鋒毫畢現,畫得十分逼真,他一步一步走近,居然站了上去,這嬌俏的戲台是真的。他忍不住唱了一段〈醉酒〉,旁邊沒有宮女,沒有太監,天上靜止的燕子悄然無聲,他覺得呼吸越來越急促,不知道哪裡來的紙漿一層一層朝他身上糊。這座書齋想要把他變成通景畫的一部分。
我醒來的時候因為手發麻,多躺了一會兒,腦子裡還彎曲著做工繁複的竹雕,竹雕的勁葉遮不住膨脹圓潤的和闐玉蟠桃。難得有機會置身那樣過分的精美,我怎麼會驚慌,忘記細細
品味書齋裡豪華的細節呢?足見我有一部分的靈魂從未被社會馴化。黃藥水似的晨光往夢境潑灑,夢中書齋的通景畫大片大片地漫漶糊爛,溫度與氣味一起死亡,我還想再照一照那面鏡子,看看是否真照不出自己?
多情的潛意識往往亂放東西,讓人明明知道在作夢,卻又醒不過來。那張看似IG留言的條幅就是好例子。或者又有一次,我打開家門,媽媽正把一隻家用瓦斯桶那樣大,黑耳朵、通身粉筆白的長毛狗死命地拖出車庫,雖說車庫鋪的是烤肉架寬的芬達橘光滑瓷磚,我也一起幫忙,但那隻怪物實在太沉重,酣睡不醒,皺眉的模樣讓我感覺牠很老很老,躲到我們家的車庫是為了等待生命完結。這個突發事件害得我上學遲到,整節早自習拿書罰站。我一個字都看不下去,想著老狗臥的地方,也是我放學後玩耍的地方,在爸爸車子返回前那是我自己的小天地,怎麼車子換成了狗?還是說車子徹夜未歸,才讓老狗有機可眠?可是那已然嚴密拉下的車庫鐵捲門又作何解釋?
不記得後續,想必是夢醒後記不清了。老屋重建後移除了車庫的設計,便很少想起這個夢。有一回母子倆散步看見一頭古代牧羊犬,這個縫綴了異樣裙邊的舊夢湧上心頭,我向她轉述,她說這不是夢呀是回憶,她看到怪物的第一眼頭皮發麻,也沒想到可怕的傢伙趕也趕不走,推起來和瓦斯鋼瓶一樣重。
潛意識不但在夢裡亂放東西,也在回憶裡亂放夢,生活裡亂放回憶。
陳芳明說過,你如何安排書架上的書,能看出你是個什麼樣的人。我的書,愛怎麼擺怎麼擺,可見我思緒混亂,但是我的混亂乃是意圖在僵硬擺動的社會體制與國家論述身上刮下一點自由,苔蘚那樣子濃綠而薄的自由,讓我能有片刻的野生,以夏日吃冰的清涼速度竄出處處粗如牛筋的秩序。除了將混亂怪罪給潛意識,或許也可以怪給星座:根據統計,我這個具有裝甲坦克意志的星座,桌上雜物競生,那些不再使用與本來無用的雜物漸漸被推擠到桌沿,等它啪一聲掉在地上,就順手扔進垃圾桶了。
和母親的對話讓我大步回到夢一般的童年,模仿那隨心所欲的孩子,隨意擺,隨意塞,也隨意打開,打開車庫,打開書櫃,打開木門,打開紗門,樓梯左面掛我的水彩畫,萬國旗似掛一排。過了幾年,紙上塗抹又擦拭的顏料開始斑駁,越來越醜,時間對孩子來說總是惡意的,在孩子的身心靈上頭剝呀捏呀讓他們過幾天就認不得自己。客廳和餐廳連成一片,放學回家手也沒洗就抓桌上隔夜的紅豆土司吃,土司裝在塑膠袋裡,我在吃它的時候,它忍不住發出窸窸窣窣的叫聲,我愣了一下,看一看,才發現有隻蟑螂在袋子裡猛踢腿。好好笑,那樣自在的年紀,和一隻鑽進塑膠袋的生命力旺盛的蟑螂。
上樓以後,出現了五公尺長的拉門,我感覺陌生,不敢拉開,努力地想才記起來這是國小高年級後才隔出來的房間,因為爸爸說我不能再和妹妹睡了。對,我想起來,一回頭,果然看見那個藏書的鐵櫃,父親把它放在這裡就是要我多讀書。我閉住呼吸,輕輕推開這片鵝油黃的塑膠門,果然是那架鐵床,蓋上木板,放上床墊,那張床是一艘棄置在鄉間荒野的雪貂色帆船,即便為叢生的雜草包圍,仍祕密陰謀成長的洪水將自己推向無岸的海洋。我坐在被褥的甲板排演電影院或錄影帶上的劇情:用彩色筆把眼皮畫成螃蟹紅,線穿過針,彈指去射床鷁上的絨毛獅子;要不然披上牡丹圖案的水紅被單當風衣,叼根牙籤,雙手比七當手槍,射向看不見的城市,告訴遠方之外的都市人我在這裡,讓我去。
浴室的門打開了,美琪藥皂的粉藕色香味攜手水蒸氣迎面給我一個大擁抱,乳色浴缸放滿熱水,漂動一只薄荷綠小臉盆,身穿雪白紡紗蛋糕裙的芭比娃娃兩手扶著盆緣,懶懶地仰躺著,她的金髮澆上熱水就會變成葡萄紫和莧菜青兩色各半,原來浴室誤認我是妹妹,預備好了一切,自動開門迎接。她熱愛「槍與玫瑰」火力四射的搖滾樂,邊聽邊唱邊嘶吼,莫非她抱著芭比娃娃泡澡時也想改變髮色,成為大都會五光十色的焦點?對九○年代的少年來說,離開鄉下是一種上進,為了離開,必須自我改造:手指遠離鼻孔,嘴角永遠上揚,講話要捲舌,英文不忘連音,中文記得用成語,每周都要對著牆上的橢圓鏡子練習,時代所向,甘之如飴。還記得疲累懵懂間打了大哈欠,正巧吸進飛過眼前的那隻黑蚊,真是好大的口氣。當自己越來越不「台」,慢慢不再「土」,或者簡單地說,不太像爸媽的兒子之後,橢圓鏡子變形成了門,我一推開就落在台北車站的天橋上,彷彿是裂開的鏡子漸漸闔攏,透過緩慢縮小的視框我眼睜睜看見房門闔上,紗門闔上,木門闔上,鐵門闔上,在最後的一束光中全部緊閉了。我轉身走在匆匆的人流亂潮中,像走在透明的浮橋,沒幾年拆除天橋,剩下記憶的虛線。
時間讓現實與記憶相對立,也讓時代與時代相對立,讓今日之我與昨日之我對立,有人稱其為進步,有人稱其為背叛。二○二二年,青年返鄉種稻是對現代進步觀念的實踐還是背叛呢?重演傳統的骨子老戲,是古代的重現抑或現代化的再現?放下對物質的思考,無條件接受藝術作品帶來的心靈與智慧的衝擊,是否又太過唯心?藝術生產的幻想誘使我活在古代與現代共同出資的蜃景中,宮殿、書畫、器物、首飾、噴水池,是催眠曲也是電子舞曲。只不過我受不了古代的帝制,帝制意味什麼都拿來,一時興起就砸爛,甲骨文的「醢」表現的就是一張把人砸爛的酷刑圖,張獻忠還吃人肉醬呢。為此我寧願沒有紫禁城、新天鵝堡,動人的紫檀多寶格、奪目的黃金音樂盒,雖然我不確定會不會也因此失去了工筆花鳥與肖像油畫,但很確定少了宮鬥戲我不惋惜。
世間事物皆對立,甚至於對立的對立,唯有字自由。即便是在最可悲的應制詩裡,字抖擻著,振振欲飛,字一旦成為其他詩行就自由了。就算是在最暗的黑牢裡徐徐圖之,字也能鼓舞眾生。木心文革時囚在地下室,「那群人」要揉碎他的肉體和靈魂,他不甘心,他說:「有了筆有了紙有了墨就有了我的藝術。」文字這種動物,古老而粗糙的表皮容易沾附各種有意無意的必然與不然,畸形而健壯的雙足醉酒似地闖蕩記憶與空間,能夠用想像力誘捕牠們的人,是有福的。然而想像力的心臟不該是自由嗎?但我近來看見幾位情願不自由的少年,他們拒絕放棄家庭提供的計畫,計畫指向的是甜絲絲的職業與錢財;拒絕走出規則清楚的遊戲設定,因為他們認為自由同時帶著風險;拒絕損失手裡握得住的物質享受,從而渴望不自由──難怪啟蒙運動發生了三百年,還能聽見重擁帝制的聲音在各國敲打。
唯有藝術自由。我愛藝術但我不愛任何國家,不愛簡單的解答。腦袋裡的每扇門都成了旋轉門,裡外明暗交替,像風車,清涼的意識流通起來,古往今來的全部對立都是調皮的雙胞胎,在轉個不停的玻璃門後面,隨機跳躍著交換位置。小說家李渝的〈躊躇之谷〉寫經歷無數戰事的軍官退伍後狂熱地沉迷於爆破工程,在一次意外中炸斷了半條腿,從此隱居在一座夢境般美麗的巒谷山林,在此重拾畫筆,回想年少時的書畫經驗,透過一次次的練習,熟悉了寫實的技巧,卻更渴望在畫紙上把握青春。他花費十多年畫下了來山中拜訪的音樂老師,畫中之人俊美無比,分不出是男是女,那凝聚眉頭的憂鬱,卻更像曾是軍官的畫家自己。肖像畫在畫家不知去向後淪為觀光酒店黯淡通道上最吸引人的補壁,繪畫鎖住悲哀,釋放了被拘禁於昔日屠殺夢魘的畫家。有趣的是,畫家遇見音樂老師前,畫不出鏡中自己的靈魂。
所以人與畫究竟是對立的,還是彼此照穿的明鏡?世上萬物的關係,或者是某種神祕的同時存在,一如畫家立足的那座「同時是天堂也是地獄」的崖谷?夢境是否就是因為日與夜的對立才成為可以任意穿越的現實?
虛幻真假難辨世界或許根本沒有想要告訴人們什麼道理,我所謂物我合一的自由、無所不能的想像,乃至於情悟的人生,或許只是提供給我和像我這樣的同類人一點生活參考──如此想法帶給我憂悒,也帶給我怖懼,特別是在力求對立的台灣。我猜想,夢中書齋那面鏡子定然是畫的,帝王家的鏡子本來就沒人照。
加入 琅琅悅讀 Google News 按下追蹤,精選好文不漏接!逛書店
猜你喜歡
贊助廣告
商品推薦
udn討論區
- 張貼文章或下標籤,不得有違法或侵害他人權益之言論,違者應自負法律責任。
- 對於明知不實或過度情緒謾罵之言論,經網友檢舉或本網站發現,聯合新聞網有權逕予刪除文章、停權或解除會員資格。不同意上述規範者,請勿張貼文章。
- 對於無意義、與本文無關、明知不實、謾罵之標籤,聯合新聞網有權逕予刪除標籤、停權或解除會員資格。不同意上述規範者,請勿下標籤。
- 凡「暱稱」涉及謾罵、髒話穢言、侵害他人權利,聯合新聞網有權逕予刪除發言文章、停權或解除會員資格。不同意上述規範者,請勿張貼文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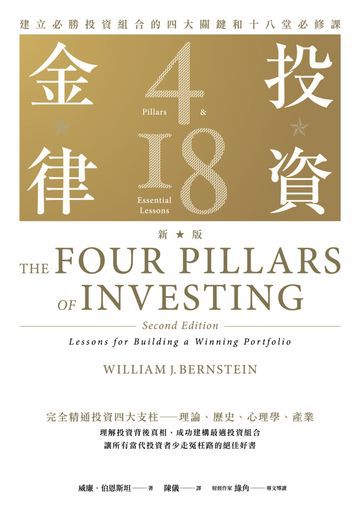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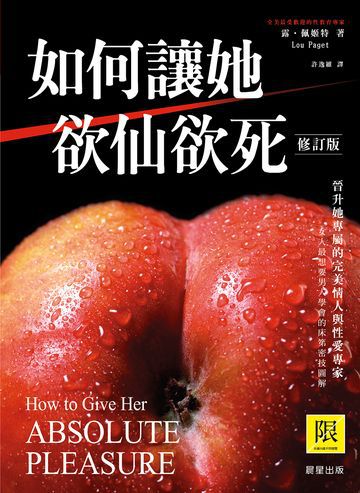




FB留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