馬翊航vs.陳柏煜/你沒有口音


專程去學口音
●馬翊航
上次在景美考族語認證測驗的時候,出現了一個口說題目:你會怕蜘蛛嗎?為什麼?我回答:「是的,我怕蜘蛛。因為有毒,而且有毛。」走出試場的時候你說:「剛剛口說題你答得很有自信齁,因為你的『mitok』講得很大聲。」mi-是能夠表示「帶有」、「穿著」、「使用」等狀態的前綴,tok是台語「毒/to̍k」的借詞。族語課堂練習的時候我特別喜歡這個詞,mitok的蜘蛛,mitok的蛇,未來說不定可以延伸成抽象的句子:mitok的念頭,mitok的男子氣概等等。因為選考語別相同,即使在同樣試場應考,我們的座位其實並不相鄰,空間安插了瓦楞紙隔板與其他語種。但即使這樣,仍然被你辨識出來:多色混雜的積木粒裡,浮出一顆暗紫的百香果。對我來說是浮球,對你來說是失效的牆。也許聽-說關係,不是只發生在對話的兩端。
類似mitok,自從學會了幾個比較長的卑南語詞彙,例如muviivii(飛來飛去)、sirusirupan(蝴蝶)、markamelrimelri(各式各樣),在對話練習中就會食髓知味、頻繁使用,它們成為了我的「主動詞彙」(太主動、會嚇到人那種)。與主動詞彙相對的是被動詞彙,亦即不會主動使用,但看/聽時,仍可以辨識出意義。但被動字彙若沒有經過書寫符號記錄,一個世代沒有使用的主動詞彙,就不可能傳給下一代——念及此事,主動一點、嚇人一點,恐怕還是好的。
有一次去初鹿外婆家,跟光蘭媽媽的朋友聚餐。香蘭阿姨說,姓馬不好捏,我們卑南族的話裡面ma開頭很多不好的,maliyay啦(酒醉)、maratrang啦(懶惰)、mavutri’啦(瞎眼)、matungatung啦(打瞌睡)、malingatr啦(頭暈),大家在板凳上撈捕拼貼這些ma氏家族的不良成員,搖晃到下一個好笑。當然開始上族語課之後,知道ma開頭也很多好字:matemuy(滿)、maderu(熟)、madalram(知道)。但即使後來學了族語,應該也不會去「糾正」這些玩笑。不只是嚴肅會破壞幽默、知識會干擾日常這樣的判斷,而是似乎有一些不那麼「古典」的使用(mi-族語?),正在生活裡發酵。
作為我的族語班同學,你聽到的ngai/話,是什麼樣的呢?
●陳柏煜
那我也分享一下我最喜歡的mi-單字好了。它們後頭連結了markamelrimelri的交通工具:搭火車midinsia、坐汽車mipaliding、騎機車miotobay——我把midinsia放進壓克力盒子當成寶貝呵護。喜歡它們的原因,出於一種難以重來的體驗。最先學會的mi-單字是服裝系列,mi-因而敷上布料的質地(日本時代的洋裁!)與穿戴的體感。在mi-的多義性尚未溶解之前,midinsia在我的腦中啪一聲打開瓶蓋,大小問號如濃密的氣泡爭先恐後:mitalupung是戴帽子,在月台接到新旅客,火車就戴了新帽子;mikavang是穿衣服,要搭上火車,只需將火車模型放進口袋。隨著新增知識「眼界打開」,我告訴自己別把它忘記,這可是母語使用者享受不到的「錯頻美感」啊!
可能好比你在試場洪亮的應答,mitok這個詞對我也有神奇的穿透力,因為台語「毒/to̍k」對生於閩南家庭的我來說,是一個「自然詞彙」,吐出它總伴隨一種忍不住的放鬆,就像清宮劇裡出現智慧型手機,恐龍裝底下瞥見肉色的人皮。
使用借詞,有個不成文的規定,那就是「要有口音」。
聽過一個(內容很可疑)的笑話。小美路過阿綢新開張的店面。小美說:「綢姊,開越南小吃店欸~」阿綢:「對啊,我還專程去越南學哩!」小美:「真的嗎,學什麼呢?」阿綢:「學口音!」說笑話的人這時會用表演刻意放大新住民「具東南亞色彩的中文會話」。口音洩漏了你的來處。可能因為當時的情境,讓我不感覺表演者意圖挖苦、貶損口音的來處,我一直以為笑話的梗,在於「不學越南文,只學越南口音」的投機取巧。
沒想到有天我能光明正大使用這個技術。練習族語篇章朗讀,老師特別囑咐:可別一遇到中文單詞就突然「字正腔圓」啊。字典要念zitēng,圖書館是tusukuwan。同樣成立的是,族語對答中,如果不得已要用中文表達你不會的詞,記得,「加上口音」!把握這個原則後,我們可樂的,把所有設想得到的日常會話都「加上口音」,幻想自己的卑南語程度一步登天——但那品味,大概不超過平時胡鬧扮演劉嘉玲、梁朝偉胡謅的粵語,以及為菜肴增添派頭的法式發音。
你專程去Kasavakan學什麼呢?學口音。那小吃部的笑話我讀來竟有點玄機。從腔體的共鳴到舌頭的鬆緊,到這些特徵引發的種種聲音習慣,不正是一種暫時擱置智識,「身體對身體」的基本練習?(聲樂老師也會提醒學生,不把氣息共鳴練到位,就直攻艱深名曲,只會落得力不從心。)匆匆兩個月的生活,族語進步幅度有限,我倒是發現,你從街坊鄰居間學到了口音。建和人說話,「這是我的」會說「這是我得(ㄉㄟˇ)」。回到台北,你處處我得你得她得。有時我覺得可愛,有時也覺得心煩:好像某些小孩會刻意模仿班上風雲人物的口頭禪,為了打入他們的小圈圈。但這樣有什麼問題呢?我自我反省。可能是因為模仿拙劣的時候,看起來很可憐。我不想你看起來很可憐。
關於學口音,我有一件不堪的童年往事。在我讀小學的年紀,學習英文普遍推崇「美式口音」,社區家長流行送孩子們到全外師的補習班上課。有一天,班上來了一位澳洲籍的女老師,陌生口音令小朋友心中「生疑」。洋娃娃(doll)成為可怕的炸彈。「Yvonne老師說的『豆』是什麼啊?」一個小男生將嘴巴豎成誇張的橢圓形。「哪有什麼『豆』,她要說的是『道』吧!」另一個小女生用講相聲般的語調搭腔。孩子們竊竊私語,煞有介事地皺眉、點頭,對Yvonne老師的「正確性」感到憂心。隔周,家長們聯合提出希望更換教師的要求。我不知道Yvonne心裡,怎麼看這群可怕的孩子。我記得最後一堂課的末尾,年輕的Yvonne老師忍不住紅了眼圈,說不出話來,負責補習班的Peggy老師出現了,一邊安慰她一邊扶著她的肩離開教室。多年後回想,我覺得自己做了一件非常卑劣的事。
文學作品裡怎麼表達口音?
●馬翊航
談口音這麼危險,這麼容易踩線,是不是要告訴你先不要?你知道的是,我七歲時候,跟著父親加入了池上戴家。有天我陪小我四歲的小表弟看書,我福至心靈、天地感通地,想用我在這個家族中接收到的「口音」念故事給他聽。念了半本,舅媽經過跟我說:「也不用刻意這樣子念。」(可能覺得我很可憐,他兒子更可憐。)
「一時改不掉」與「模仿」是關於口音的兩個狀態,口音的危險,因為它與當下的「位置」、過去的「境遇」、未來的「走向」糾纏在一起,也常常連接不善意。我到現在打球、游泳、丟掉,發的音還是有點偏移。但我喜歡口音,口音是接觸與記憶。當然我念故事書的例子不是一個很好的例子,可我才七歲啊——不過這可能比建和式的「的」,更貼近你說的「加入」某圈圈的期待。
文學作品裡怎麼表達口音呢?王禎和〈嫁妝一牛車〉裡的簡底,是鹿港腔的,阿好說他「說話伊伊哦哦,簡直在講俄羅!」;楊牧《山風海雨》裡的外省女老師,氣流摩擦唇齒,「『去去去,去遊戲。』一連四個蹙嘴音,我瞪著她好看的唇角,很快就入迷了。」高英傑《拉拉庫斯回憶》裡寫從前部落裡外省司儀的口音,總把「鞠躬」念得像「郭恭」,聽起來像「kokongu」,是鄒語裡的攀木蜥蜴,公家集會常因為族人的笑聲而卡頓;黃崇凱《新寶島》把部分對話直接转换成简体字,不神奇,但看上去就有声音了。朱惠足翻譯目取真俊的〈水滴〉,也花了許多工夫把沖繩話的語感「翻」出來……想得到的例子有很多,但使人感覺「沒有口音」的文學作品也很多嗎?
大一語言學概論的時候,某次課堂有關於口音、腔調的討論。一位中文系的德國同學發言了。(他華語極好,在台北打電話給房東約看房,現場見到他本人,房東總是一臉詫異再三確認。)德國同學說,「你沒有口音」是他在台灣最常聽到的一句話。但理論上,每個人都有自己的口音,所以並沒有「你沒有口音」這回事。回到去越南學口音的笑話——梗在投機取巧,可能也在大費周章。
張亦絢《永別書》的附錄,她回應孫梓評,關於《永別書》是否可以是某種國族寓言以「代言」台灣,她說與其是「寓言」不如「欲言」;更接近「帶言」而非「代言」,「因為我關心的是語言的可能性,而不是完好的論述」。我們在此談論「口音」,我也希望是「帶言」的:夾帶、走私、暗藏、導流。比起聽覺,也許更接近觸覺。你在「地下室錄音」系列裡的〈陽台的投稿〉不就是這樣?「在那些停頓裡,他的心中有一名不通人情的批評家正重聽著方才的嘗試。他彷彿捧著碰了許多小凹洞的鐵鍋子。手指經過一個凹洞,心口就痠一下。消失的東西總比它原有的維度再多一個維度。」
如果能被這樣理解就太好了
●陳柏煜
關於暗藏、走私和夾帶。
來到Kasavakan,我一直沒辦法有效回答旁人的提問:為什麼來學卑南語?我的標準簡答是:為了寫作。倘若「太高深」的作答冷卻了對方的興致,我會趕緊補充,「有點像是收集資料啦」。這樣模稜兩可的報告,像是「施工中」的告示牌,阻擋來人繼續前進;我會不會聽起來,太像個Payrang,漢人aka歹人(台語)?他們為什麼要提供資料、交出知識,如果我無法證明自己足以信任。如果我看起來像是暗藏凶險的鈍色水面。也許,我會暫時被歸為「來部落做語言學、民族學田調的研究生」?也許,暗藏在叔叔阿姨心中的答案是:身為你的男朋友,我是「為了你來」?如果能被這樣理解就太好了。因為在日常中談論「寫作」是羞恥的,解釋它不是讓它顯得虛情假意,就是讓它顯得虛無縹緲。我們也不談論「色情」。因為它們攪動說話與感官暗藏的水面。想想這麼說該有多滑稽:不是為了你,也不是為了卑南語,我關心的是語言的可能性啊!
結束Kasavakan兩個月的短住,馬爸從池上開車來幫我們載行李,生活雜物大大小小拼七巧板般擠進後車廂,我們在叔叔家吃餞別的午餐。席間,喝過小米酒的叔叔出其不意拉住馬爸,前言不搭後語的拉高聲調:哎呀,也是kituruma'an,我們現在都很OK的。馬爸紅著臉舉杯呵呵笑。他當然知道ruma'是「家」,而kituruma'an是指成為家人的「配偶」。(不知道叔叔是不小心說溜了嘴,還是故意趁著酒意說給他聽?)祖先的智慧沒讓男婚女嫁限制造字的法則,迅雷不及掩耳,kituruma'an順利走私過關了。
夏天我和你去初鹿的家探訪外婆,摩托車轉進有楊桃樹的小院子,車才熄火,熱天的蟲鳴馬上填滿多出的空隙。屋裡傳來外婆高聲喊eman(誰)?我們看見她從紗門內狐疑探查,猜測是郵差、社工還是其他人。「滾滾啦!」你回以小名。視力聽力退化的外婆,像鼴鼠般困惑警戒,直到你拉開紗門才展露笑容。獨自在家又無力照顧菜園的植物,看電視是外婆每天唯一的正事。它就像天線寶寶肚子上的螢幕在恆久不變的藍天草原中剝出整個現實世界。在屋裡陪她看電視時,電視也是招待我們的一塊鳳梨酥,周圍崩裂發亮的碎屑。可怕的寂寞使我們侷促不安,提早向外婆說再見。外婆不捨,抱住滾滾,也抱住我(滾滾的同學),皺巴巴的眼角濕潤起來,說不知道什麼時候才能再見。這時你記起要給外婆的零用錢,把事先準備好的小紅包羞澀地塞進她手裡,彷彿那是一疊情書。外婆連忙搖手說不用啦你不要給我錢。不知道哪來的靈感,你摟住她的肩告訴她:ulra ku paisu(我有錢)!突然夾帶的族語像是給驚訝的外婆注入了力量,好多凝滯的、講不清楚的情感,都變得簡單明瞭;此時你才把正確的東西放進手裡。捏著的小紅包就不推回來了。這是我關於夾帶的小故事。
九月《文學相對論》 黃春明vs.羅智成 將於9月5-6日登場 敬請期待!
加入 琅琅悅讀 Google News 按下追蹤,精選好文不漏接!逛書店
猜你喜歡
贊助廣告
商品推薦
udn討論區
- 張貼文章或下標籤,不得有違法或侵害他人權益之言論,違者應自負法律責任。
- 對於明知不實或過度情緒謾罵之言論,經網友檢舉或本網站發現,聯合新聞網有權逕予刪除文章、停權或解除會員資格。不同意上述規範者,請勿張貼文章。
- 對於無意義、與本文無關、明知不實、謾罵之標籤,聯合新聞網有權逕予刪除標籤、停權或解除會員資格。不同意上述規範者,請勿下標籤。
- 凡「暱稱」涉及謾罵、髒話穢言、侵害他人權利,聯合新聞網有權逕予刪除發言文章、停權或解除會員資格。不同意上述規範者,請勿張貼文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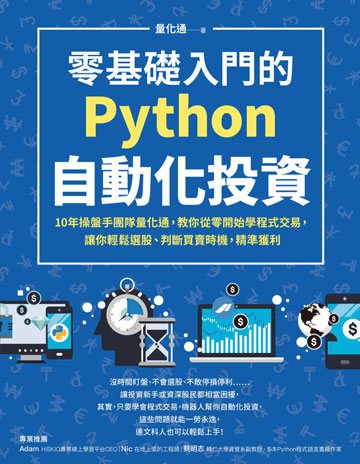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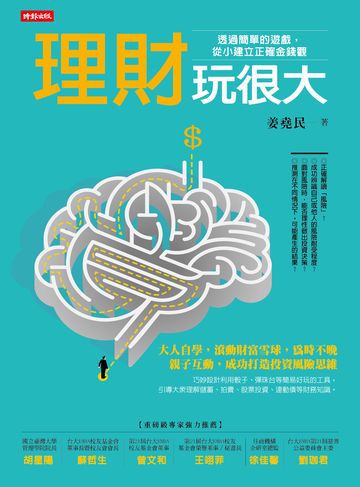




FB留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