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宇軒/知情同意書

1.
敲門、脫鞋、進入、坐下,這是進入實驗室前的流程,自帶一種人工的儀式感,告訴自己現在所身處的空間已經不一樣了。
在內容五花八門、時間安排不定的大學生活裡,「參與實驗」也許是一種認識世界、認識自己的方式。不同於「填寫問卷」那種不知真假的資訊性調查,在一個固定的實驗環境裡,透過儀器記錄感官的活動,這種體驗對過去從沒接觸過的自己來說,是一件非常新鮮的事:以往總是在課本中背誦、研究著別人,現在竟然變成別人要研究我。
在實驗裡出現的詞語都是被解構的資訊,所有意義都指向我,所有的回答都沒有所謂的對或錯。在這裡,所有人都只能是自己,為了一點點錢,在約定的時間內任人擺布,用小小的自由試著說些什麼。這樣說感覺像是出賣自己的身體,但參與實驗最大的目的,說實在不外乎就是貪圖那少少的受試者費用(運氣差一點就只有超商禮券)。
在自己參與過的各種大小實驗中,最常見到的儀器是「眼動儀」──將下巴靠在電腦前的架子上,雙眼凝視白色螢幕正中心的黑點,黑點會以幾秒變換一次的頻率在四周輪流出現,最後再回到中心,像是家,旅行的第一站和最後一站。離開自己的舒適圈,揣摩自己以外的萬事萬物,然後回到原點,像一個命定的迴圈。實驗也是一種旅行。
黑點的規律在來回追蹤數次後,儀器便會自動偵測視線的角度;而當機器追蹤到視線,便能確認受試者的眼睛正在盯著螢幕上的哪個地方,正式的實驗便得以開始進行。
看似抽象的視線在儀器的測量之下變得無比具體,這時才知道「它抓住了我的眼球」可以不只是修辭中的誇飾法。
2.
做實驗,就像重新安排宇宙的秩序。
在眾多的實驗中,關於「認知」以及「多工處理」的主題一再出現——無論是同時進行很多件事,或者是在事情之間來回切換注意力,似乎都是研究者們時常關注的研究題目:記住毫無關聯的數字順序、益智遊戲的邏輯推理、圖文認知的閱讀測驗等。多麼殘忍,他們竟然讓一個文組的學生去閱讀困難的數學與科學知識──儘管他們說這是「科學普及」──一切都在考驗我遠遠不足的智慧。
其中一個令我印象深刻的實驗,主題和「詞語聯想」有關。實驗進行的過程堪比一場猜謎大賽,受試者必須根據電腦所給出的三個提示詞,在極短的時間內猜出背後的解答,比如:喜帖、攻擊、武器,答案是「紅色炸彈」。在範例問題之後,電腦隨即向我丟出一堆堅硬的詞彙:海洋、河流、噪音、火山、岩漿、醜聞……詞彙突然間巨大了起來,儘管我無法辨認,但卻仍然能隱隱感知它們的連結──金屬般堅硬,而不允許任何質疑。
實驗成功了,詞語一個接著一個地輪流把我砸死,到下一題時我復活,又被砸死,又復活。一切按步驟進行實驗應有的繁複禮節,當我試著說些什麼,它就打散一切秩序,亂糟糟。
也許宇宙本來就是亂糟糟的,刻意安排秩序反而顯得莫名其妙。
關於眼動儀的實驗,通常會配合著鍵盤的按鍵。實驗室裡,他們播一小段聲音,要我針對自己情緒的愉悅和強烈程度進行評分。我按著鍵盤,聽著一段段風聲、雨聲、爆炸聲、眾人的笑聲、做愛時的呻吟聲、被毆打的哭泣聲,包含人體和非人體所發出來的。在聲音之前,螢幕會隨機顯示綠色或紫色,到底什麼意思我也沒有明白,但我總能感覺出他們正試圖要說些什麼。我聽著一切,在被黑色布幕重重包圍的暗地裡,持續地摸索鍵盤,輸入自己情緒的愉悅和強烈程度。
整個世界微縮在小小的耳機和螢幕中,除此之外是一片黑暗。
3.
除了眼動儀,有時當然還會出現其他奇怪的儀器。
在一個超聲波的舌位檢測變化實驗中,他們要我手拿金屬機器抵著脖子和下巴間的區域。我看著螢幕中的舌頭,當我說話時它就跟著動。是誰在控制我呢?後來他們得寸進尺,要求我在時間內念出一個又一個的繞口令,試圖讓我的舌頭打結,同時發出所有正確、清楚的聲音。實驗結束後,我便好像什麼都不記得了,只感覺下巴內側仍舊抵著金屬的儀器,舌頭隱隱地冷冰冰。
確切的位置應該不算是下巴?和朋友爭吵著那個地方到底叫什麼:頷?下巴裡面?就是脖子和下巴之間的區域,掐別人脖子時,手掌虎口抵住的位置。朋友說那一整個都叫作下巴啊,整個臉底部的大平台都是下巴。我說是嗎?人體真奧妙。
記錄舌位變化只需要身體單點的測量,而其他更多的實驗需要測量人體的心跳、血壓,或者是更細微的生理反應。
當實驗通知信件提醒「著輕便服裝」時,往往就代表著需要我提供身體,讓他們「安裝」這些設備:用金屬圓點貼滿我、用小小的夾子夾住我、用繁瑣的線路纏繞我……突然間,我便置身於一座廢棄的醫院內部,不斷有恐怖的聲響從周遭傳來,我只能艱難地用鍵盤與滑鼠控制自己的行動。這時的我早已不是我,而是一位愚笨的機器人,連簡單的遊戲都無法破關,還不斷被其中的音效嚇到。
在身上纏繞如高壓線的線路、張貼如告示牌的金屬點,這些都還不算什麼,畢竟當一根稱職的電線桿一個多小時並不困難。最麻煩的實驗,莫過於需要測量腦電波的那種。
當我坐下後,實驗人員為我戴上電極帽,用平口針在我的頭上注射傳導膠。你看它黏黏的,像膠水。要不要摸摸看?這是為了可以讓腦波的訊號更容易被蒐集,不用太擔心。等等我們會重複這個動作六十幾次喔,他們這麼說,眼前的點點紅色便一一變成淺藍色。身後投影機的光打在我和他們的身上,我就這麼看著針頭的影子在我頭皮的影子上使勁地鑽。「由於實驗室裡沒有洗頭設備,實驗結束後我們會提供濕紙巾與衛生紙;若您會介意,可以自行攜帶帽子實驗後穿戴。」恍然想起實驗通知如此寫道。
「大家都很喜歡大衛準備的地球」、「貓在鏡子裡睡著」這些詩意的文字算錯嗎?他說算。我一輩子都在做錯的事。轉眼我已經拿著受試者費用站在實驗室外——頂著滿頭的問號,以及傳導膠。
4.
參加了這麼多實驗,只當受試者也太無聊了吧?在社會心理學的課程,我和同組的同學為了期末報告,規畫了一個不那麼嚴謹的實驗。
簡單來說,我們邀請了兩組人馬:一組是與施測人員認識的實驗組,另一組則是不認識的陌生人作為對照組。當大家輪流進入教室、依序入座後,我們便提供他們施測的問卷以及綠茶,並播放認知記憶的影片讓他們填答。
是鹽巴,我加了鹽巴。
原本平淡且帶有澀味的綠茶在經過調味後,味道變得奇怪而詭譎,有點像壞掉的梅子綠茶。實驗過程中,我們必須拐彎抹角地「提醒」受試者:口渴的話可以飲用我們提供的茶水喔!無論如何,死也要讓每個人都嘗到一口鹽巴綠茶。
假的認知記憶影片結束後,我們發下匿名的表單讓大家填寫,其中包含茶水的滿意度;離開實驗教室的門口時,再分別詢問每位受試者對茶水的滿意度。
你們這群大騙子!他們笑著罵道。
他們的確有資格這麼說。在實驗結果的統計中,認識施測人員的實驗組無論在匿名問卷或是口頭詢問時,都誠實表現出茶水很難喝的感受;而不認識施測人員的對照組則反之。在生命中能夠認識不需要客套、不需要把「不好意思」掛在嘴邊的人,是多麼難得的事。
把綠茶倒掉之前我又喝了一口,味道鹹鹹的,像騙子的眼淚。
5.
對受試者來說,有的實驗在螢幕顯示「實驗結束」時就結束了,而有的實驗在離開實驗室後還在繼續。
在所有參與過的實驗裡,讓我最備感壓力的反而不是那些需要使用眼動儀、傳導膠或舌位檢測儀的實驗,而是只有進行錄影記錄的實驗。錄影,一種無聲的監視,我們被迫卻又主動地做出眾人所期待的舉動,所有的錯誤都一覽無遺。一次,參與一個「模擬旅行」的實驗,只是在電腦前控制游標,依據時間和人數縝密地規畫,透過網站將機票、旅館、門票全部準備完成。整場活動比起一群人快樂出遊,更像是一個人試著說話。
想當然的我又搞砸了。實驗結束後,我少訂了一個人的機票,像是自己被留在了不知名的地方,再也回不來。好險只是實驗,不是人生。
每完成一次實驗,就像是完成一趟旅行。無數個眼動儀的黑點回到中心,然後消失。實驗結束,那些被我偷偷學起來的口音練習、物理題目、地科知識、數學邏輯都在腦袋裡冬眠,等待一個時機再次冒出頭,隱隱閃動:電位差、淨電荷、束縛力。潮濕的空氣因為有水,所以不容易產生靜電。他們要我回答,要我自我解釋。
「最後一個問題。如果過去有這樣的機會,你會希望能夠多練習自我解釋嗎?」實驗結束的訪談裡,他看著我的眼睛,語氣堅定。彷彿詢問的對象並不是我,而是住在我軀體深處,一尊顫抖的神靈。
人海茫茫,每一滴水都曾是另一滴水,每一滴水也都將是另一滴水。世界一直透過這些大大小小的實驗,試圖讓我明白:我也是水做成的,我只存在於這個瞬間,迴環反覆。
想起每場實驗的開頭,他們遞給我知情同意書,讓我仔細閱讀。所有簽名都必須負責,我必須把握時間去認識世界,認識自己。我應該要試著去說些什麼,無論對錯,在這個實驗的小房間之外,不說話就沒有人會管那麼多。活著不過是一場大型的社會實驗,每個人都無可避免地是實驗人員,同時身兼著受試者,在不可逆的過程裡出賣自己;嘗試丟掉什麼,得到什麼,直到成為社會化的另一個人。所有實驗的最後,沒有人會記得你是誰,能留下的不過是一個禁得起反覆驗證的結果。
加入 琅琅悅讀 Google News 按下追蹤,精選好文不漏接!逛書店
猜你喜歡
贊助廣告
商品推薦
udn討論區
- 張貼文章或下標籤,不得有違法或侵害他人權益之言論,違者應自負法律責任。
- 對於明知不實或過度情緒謾罵之言論,經網友檢舉或本網站發現,聯合新聞網有權逕予刪除文章、停權或解除會員資格。不同意上述規範者,請勿張貼文章。
- 對於無意義、與本文無關、明知不實、謾罵之標籤,聯合新聞網有權逕予刪除標籤、停權或解除會員資格。不同意上述規範者,請勿下標籤。
- 凡「暱稱」涉及謾罵、髒話穢言、侵害他人權利,聯合新聞網有權逕予刪除發言文章、停權或解除會員資格。不同意上述規範者,請勿張貼文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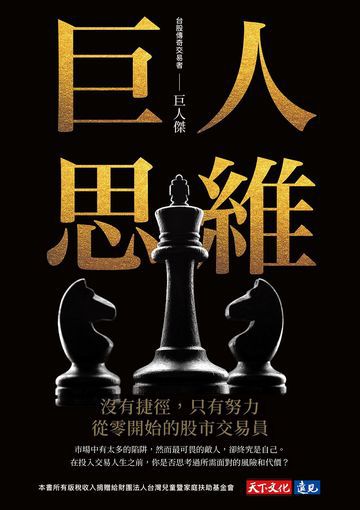




FB留言